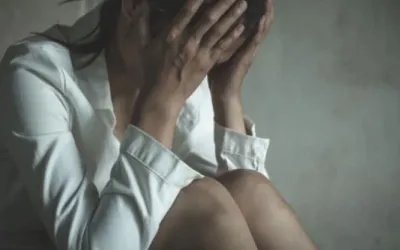原文刊載於《國家治理》2015年第8期
標題:依託網絡平台空間凝聚社會正能量 新加坡網絡治理策略與邏輯
作者:周兆呈博士
作者簡介
周兆呈博士,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原主編,新加坡江蘇會會長,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教授,資深國際媒體專家,曾任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SSAS)會長,現為海底撈國際控股首席戰略官。
網絡治理的全球化挑戰
人們普遍認為傳統媒體可以扮演社會公器的角色,傳播信息的同時提升民眾思辨能力。然而,作為傳播的新興平台,新聞網站、個人博客、社交媒體等除了將傳統媒體的功能放大發揮之外,同樣也可以通過內容和觀點來源的廣泛、參與者的多元,以新的平台提升民智,提高人們的思辨能力、認知能力以及邏輯能力。
在新加坡,社會成員可以直接使用英文世界的臉譜(Facebook)、推特(Twitter)或是華文世界的微博、微信平台,這是長期扮演東西方文化交匯地的新加坡,在網絡新領域再次得以發揮自身特長的重要原因所在。新加坡的臉譜Facebook用戶已經達到300萬,超過總人口的一半。與此同時,國外社會群體通過社交媒體對各自國家和政府進行監督、批評、質疑,所採取的語言、方式、力度,也必然會在某種程度上對新加坡的網絡社群產生示範或借鑑效應。
傳統媒體向社交媒體的過渡轉型,雖時間短暫,但網絡媒體或平台卻日益展現出驚人的滲透和裂變能力。民眾藉助這一平台的表達,聲音集聚的能量越來越得到凸顯。信息傳播可以實現知曉、鼓動、宣傳、教化的不同作用,直接影響政治的發展。這是媒體和政治關係的體現。透過社交媒體生成的觀點、分享等傳達出海量信息,打破了傳統媒體的信息壟斷,但人們對事件的關注、看法與評論的 短暫、零碎特質,使得信息龐大而混雜,容易造成「金玉 良言」與「泥沙俱下」同在的局面。在這個意義上來說, 全球政府共同遭遇的是一個全新領域的挑戰。
在民意迅速、大量的爆髮式呈現中,信息傳遞具有 碎片化、歧義化等特徵,事件往往出現不止一個「版本」 或被扭曲的現象。一個民生事件容易在各方民意「萬馬奔 騰」下發酵,引發公共危機。網絡時代的民意,比以往任 何時候都複雜。多元化的新媒體及其運作模式,導致多元 主體對輿情產生不同的拉力。這些真知灼見或一家之言, 都成為影響議題走向和最終結果的力量。
「社會參與的全球化」,蘊含了政府與民間對話關係 的深刻改變的可能。面對網絡帶來的「利」與「弊」,政 治人物必須接受,讓自己適應網絡時代的要求,習慣網絡 世界裡的「習慣性」批評,坦然面對嘈雜與多元的聲音。這就需要執政者在社會治理領域具備新的思維意識,並通 過社會機制和法律手段確保網絡平台空間有利於社會正能 量的凝聚。
新加坡網絡治理的「平衡」策略
在新加坡,因為生活觀念的改變,民眾的社會表達 和政治參與這些年也發生相應的改變。近年來的房價、交 通、教育、新移民以及數位高級公務員涉貪腐等問題,激 起了不少批評聲音。各類聲音和訴求的分貝不斷增加,在 某種程度上是社會觀念發展到新的階段的一種體現,也正 是因為網絡載體和社交媒體的發達,使得民眾表達意見更 為容易和便捷。
新加坡政府的網絡治理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方面積極藉助新媒體平台與民眾進行溝通,另一方面採取不封鎖、不屏蔽、以法管網的策略,力圖達到「用」與「管」之間的平衡。
在利用網絡接觸民眾、打造信息化路徑上,新加坡的做法既有機制化的政府部門網絡平台,也有個性化的政治人物網絡平台,從而兼顧上情下達的順暢,以及打造政治人物的社會媒體化特色,體現人性化、年輕化溝通的需求。截至2012年底,新加坡政府各部門已經設立229個facebook頁面、92個Youtube頻道、86個Twitter戶頭、20個博客、59個手機應用,始終保持政府與公眾間的積極互動。新加坡政府很清楚,新媒體時代的選民是和上一代不一樣的,對待民眾思變求變的訴求,政府必須作出積極和必要的回應,以變應變。同時,政治人物也積極打造個性化的網絡溝通渠道,通過個人的臉譜等社交媒體,分享生活點滴、活動更新、出國參訪等細節,使用極具個人特色的語言和文字與民眾保持活躍的互動。目前,包括總理李顯龍在內的國會87個議員都開設了個人的臉譜戶頭。
此外,如何應對網絡輿情,成為考驗新媒體時代新加坡政府執政能力的新指標。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早在2010年就明確指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不會被網上一些虛構的反饋或受操縱的輿論所影響,同時他也指出,如果新加坡人希望政府認真看待,就應以負責任的方式來傳達自己的意見。
一個例子是「人工草皮」(astroturf)現象。2010年,新加坡房地產市場備受爭議,李顯龍總理和多位部長都收到多封電郵,批評政府沒有盡力抑制房地產價格上漲,要求政府快速並大幅度地降低房地產價格,否則下次大選他們將不再支持人民行動黨政府。這些電郵論點相同,用詞具說服力,風格也一致,並附上姓名和地址,甚至附上身份證號碼。
由於電郵內容和語調過度相似,新加坡政府覺得事有蹊蹺,於是邀請對方見面討論,然而卻沒有收到任何回復。在核對來郵者的姓名和身份證後,發現其身份都是虛構的。李顯龍表示,「我們預見這樣的『人工草皮』現象會不時出現,所以我們得分辨出什麼是真的草,什麼是人工草。政府必須懂得這麼做,公眾也一樣」。對於網絡普及化使網上很容易形成輿論風潮的現象,李顯龍認為,「我們做決策時,在分析這些電郵或網貼時,不可能按照所收到的意見當中,多少則是支持的、多少則是反對的,進而計算出支持者有理或反對者有理。我們必須了解這些意見代表什麼」。
顯然,網絡的便利使得製造假象和傳播虛假的成本極為低廉。網上造假現象由個人、廣告、公關公司、政治團體所發起或操縱,卻在過程中技巧性地掩蓋真正的幕後源頭,讓社會大眾錯以為是民眾或社會草根階層所發起、反映民間的心聲和意見。而對待藉助網絡製造或傳播虛假民意,官方部門如果也利用「水軍」進行「反製造」,表面上看似雙方扯平,但其實會付出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代價,使得輿論更為真假混雜。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熟悉網絡特性,繼而對網絡民意做出準確的判斷。
另一個例子是2012年7月,新加坡警方接到報案,指有人在臉譜及推特上發表有種族歧視字眼的言論,對馬來族也有明顯輕蔑態度。經過調查後,兩名17歲新加坡華族在籍男子被捕。新加坡警方當時發表聲明說,任何威脅種族與社會和諧的行為都可算觸犯煽動法令。根據煽動法令,初犯者可被判罰款最高5000元,或監禁最長三年,或兩者兼施。一位高級警官在聲明中表示,「言論自由的權利並不 包括可能引發種族或宗教信仰的摩擦或衝突的言論。雖然 網際網路是一個表達個人意見的便利管道,但公眾也應切記 須為在網上的行為負責。警方認真看待這類破壞社會和諧 的行為」。
第三個例子是2012年7月,新加坡總檢察署與一位知名 博客主的交鋒。這位博客主在網文中認為一位整形名醫觸 犯法律後的判刑過輕,因此質疑案件的司法程序和判決結 果。他也談到一些網民對此案的不滿,認為對財力豐厚者 可行使另一套法令條文。新加坡總檢察署隨即發表聲明, 指出該博客聲稱「新加坡法庭偏向人脈關係廣泛者」和 「新加坡司法體制長期偏頗」,都是虛假和惡言的指控, 這些嚴重指控已對法庭造成誹謗。在解釋了相關刑罰的法 律依據後,總檢察署正式致函,要求該博客主在五天內把 博文從網上摘下,並聯同總檢察署信件在網上刊登道歉, 否則總檢察署將對他展開藐視法庭的訴訟。該博客主隨後 從網站刪除博文,並刊登公開道歉信,向司法界表示歉 意,保證不會刊載造成相同或類似影響的博文。
對網民超越底線或是有可能破壞現有秩序的言論,雖 然採取強勢態度,但由於新加坡政府部門依據的是既有的 法律框架,同時民眾具有高度的法律意識,因此政府部門 的這些反應,在新加坡社會能夠獲得理解與支持,網民也 從當局者一系列執法行為中認知網絡的行為邊界。
新加坡網絡治理的政策邏輯
網際網路不再是專屬於經濟領域的投資對象,更是社會 領域改變社會生態的重要推動力量。網絡時代開啟了政府與民眾的全新互動模式,對於掌握或主導社會絕大多數權力的新加坡政府來說,面臨著「質」的改變。民眾通過自媒體的表達空間改變訴求方式,並在網絡平台上尋找同聲共氣的取暖對象,形成意見的集合,匯聚成具有一定聲勢的民意。
事實上,網絡上民眾話語權的擴大,消解和削弱了執政者過去得以壟斷或強勢擁有的話語空間。民眾話語權的擴大,體現了對政府的更多質疑、更廣泛的社會參與、新型的政府與民眾間的契約關係。這種契約關係推動執政黨和政治人物的自我革新,網絡話語權的分薄,意味著社會權利和權力架構的另一種分配。
新加坡執政者所展現出的新媒體思維,以建立政府與民眾間即時、順暢、寬容、平等的新型溝通關係為依歸。因此,新加坡網絡治理政策,一方面遵循較為開放的姿態,維護民眾自由表達的權利,既顯示其了解和順應新媒體時代民眾需求的變化,也體現其善加引導和利用民意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則以法律的約束向民眾傳達非常明確的網絡使用原則與界限,達到治理網絡的目的。
除對新聞網站的運作制定新的條例之外,社會不同領域的個人博客或網絡論壇等,內容和觀點雖然是五花八門,不受傳統媒體的采編專業原則的限制,但受限於新加坡社會不同領域的相關法律,比如《誹謗法》、《煽動法》等法令。這使得新加坡現有的相對完善的法律機制在網絡時代同樣起到維護社會輿論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及遏制惡意言論使其不至於肆無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