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朋友原本閒聊著周末發生的事情,突然演變成源源不斷分享自身家庭問題的具體細節,友人一絲不苟地揭露他過去與毒癮作鬥爭的經歷。
一名朋友經常三更半夜打電話給你,向你傾訴痛苦的童年記憶和經歷,而且往往還繪聲繪影、細節令人難受,讓你感到很不自在。
你可曾做過以上類似的事情?還是曾有人這麼向你傾訴「心事」?
乍看之下,上述例子似乎只是一個人傾訴或發泄心中的不快。不過,因話題太沉重,而且分享時間和地點不適當,這樣的行為可被視為「創傷傾倒」(Trauma dumping)。
Trauma dumping直譯是「創傷傾倒」,指一個人將創傷性感受、自己的困難和壓力傾倒給另一個人,讓對方處理超出他們能力以外的情緒。這是一種沒考慮傾聽者是否有能力消化這是負面情緒,單方面地把個人的強烈情感卸載的行為。
不同於平日裡的相互性的情緒發泄行為,創傷傾倒一旦發生,處於接收方的人可能會感到一定的不適與壓力。
Heartscape Psychology創辦人兼首席臨床心理學家廖詩敏向《今日報》進一步解釋「創傷傾倒」現象時說,當一個人傾訴創傷時,他們分享的話題通常是過於私密的,包含過多的個人信息,導致處在接收方的人,感到不知所措和無助,並可能觸發屬於他們自己的個人創傷。
周泳伶臨床心理診所的諮詢心理學家蘇儀玲則指出,雖然分享煩惱被視為人與人建立聯繫的一種方式,但創傷傾倒可能會破壞人際關係,因為傾聽者可能會覺得有心理負擔,好像分享的人在「傳遞」創傷,或者覺得自己有責任「拯救」對方。
如何分辨對方在發泄情緒還是「創傷傾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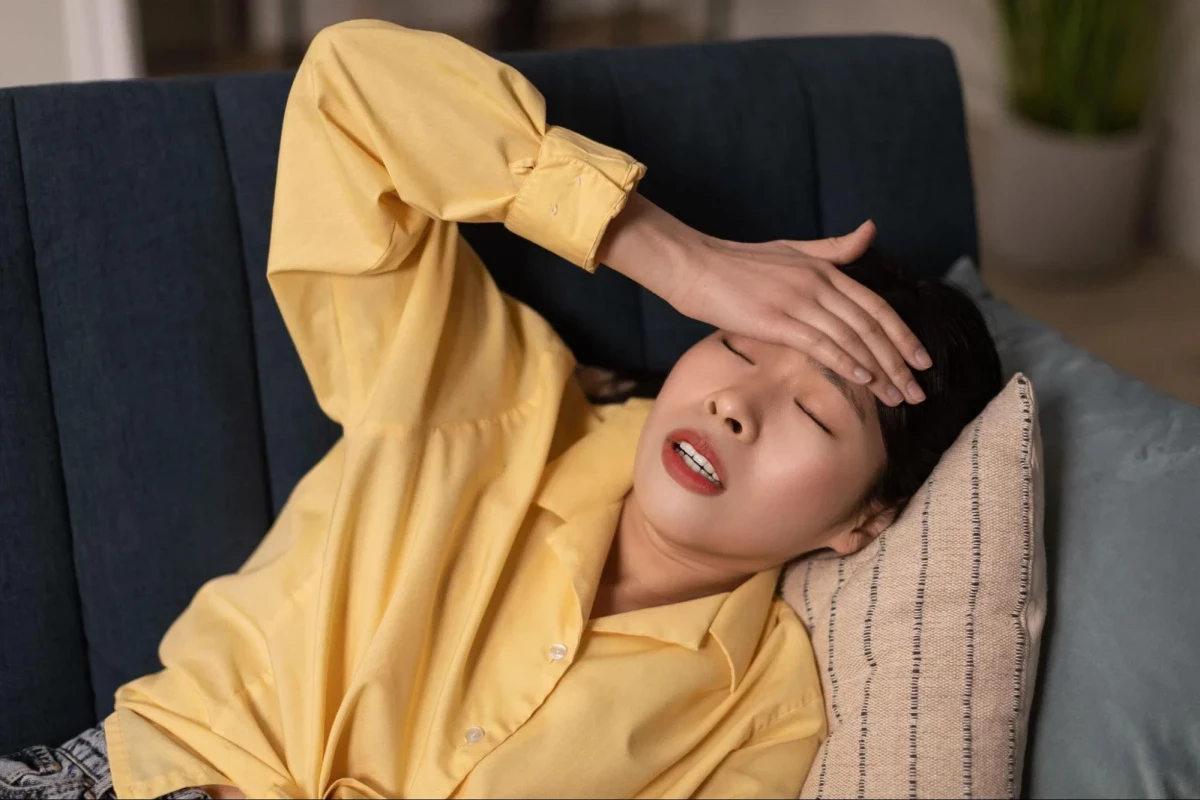
(ALAMY)
創傷傾倒和發泄情緒的共同點是為他人提供一個釋放被壓抑情緒的出口。
索菲亞健康診所的心理治療師黃慧瑜指出,創傷傾倒的一個明顯跡象是,說話者過於專注於「卸下」他們的創傷經歷,而沒有察覺傾聽者的負面情緒接受度。
醫療科技起步公司Intellect的臨床心理醫生Julia Khaw說,另一個關鍵的區別是,發泄通常是在一個更平等和互惠的對話中表達情緒、挫折或擔憂。這是一種雙向交流,雙方自願參與,不像創傷傾倒那樣,其最終目標只是想達到單方面釋放個人情緒,尋求理解或獲得支持的結果。
蘇儀玲對此表示認同,她說,在發泄時人們往往會相互分享或交流,促進彼此的信任和聯繫。
創傷傾倒則往往是單方面的。傾聽的那方通常沒有任何機會分享或參與談話,是一個很有距離感的體驗。
蘇儀玲解釋說,儘管發泄和創傷傾倒似乎有一些重疊之處,創傷傾倒往往涉及「敏感和令人不安」 的「情緒強烈的信息」 。相比之下,發泄情緒通常涉及不那麼強烈感受的經歷,而是一些日常生活上的挑戰或轉變所帶來的壓力。
她補充說,創傷傾倒的人可能不完全了解他們分享的意圖,即便在不合適的時間或環境下,也覺得非分享不可。
「創傷傾倒」的人很自私?
處於心理創傷傾倒狀態的人,因在談話占據主導地位,讓人覺得他天生就是自私型。但專家指出,他們其實是在情緒上不堪重負,必須找人將之「卸下」。
廖詩敏說,對創傷傾倒的一個常見誤解是:這些人就是在尋求關注和想操縱他人。
「其實,我們需要明白,經歷過創傷的人需要他人明白自己的經歷和感受,並且努力調節自己的情緒。」
她說,情感上不堪重負的人往往無法察言觀色,更不會先提醒他人,自己即將分享一些可能會引起對方不安的話題。
蘇儀玲也說,創傷傾倒是需尋求心理專業人士幫助的跡象。朋友、家人、甚至網絡上的社群都不是求醫的替代品。事實上,心理健康專家的工作就是處理這些創傷。

有「創傷傾倒」傾向的人應該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ALAMY)為什麼「創傷傾倒」會導致友情破裂?
心理學家說,創傷傾倒會損害雙方的關係,無論是新建立的還是建立已久的關係,因為這種分享是越界的表現。
大多數時候,聽別人創傷傾倒的人並沒有同意接收這些信息,也可能沒有判斷和選擇要不要聽的情感能力。
黃慧瑜就說,那些發現自己一直處於創傷傾倒接收端的人,可能會感到疲憊、怨恨或無助,並開始避免與對方交流或疏遠對方。
此外,一些人可能會認為,創傷傾倒是一種「自我表達和展示脆弱的健康行為」 ,可以與他人建立更真實的聯繫。
黃慧瑜駁斥了這一點。她說,創傷傾倒往往會造成一種單方面的、有壓力的、不平衡的關係,因而抑制真正的親密關係。在這個過程中,聽者可能會因為對方所分享的內容的負面性質而感到不舒服,甚至不知道如何回應。
廖詩敏說:
「對於那些高度共情且沒有明確情感界限的人來說,他們在聽創傷性內容時可能會經歷替代性的創傷。」
「向新認識的人創傷傾倒,會立即產生不平衡和單方面的問題,這與建立新關係所需的相互性、互惠性和信任背道而馳。」
如何確保自己不創傷傾倒,也不當別人的「情感垃圾桶」?
如果你認為有人在向你創傷傾倒,甚至向你發泄:
可以設定一個固定的或預先計劃好的時間段,在自己有足夠能力去消化負面情緒時,才去當對方的「垃圾桶」。
可以要求對方在談話中省略某些細節。
如果你是要分享創傷經歷那一方,在分享時先徵得對方的同意,詢問是否可以進一步討論創傷細節,以及詢問聽眾對信息的接受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