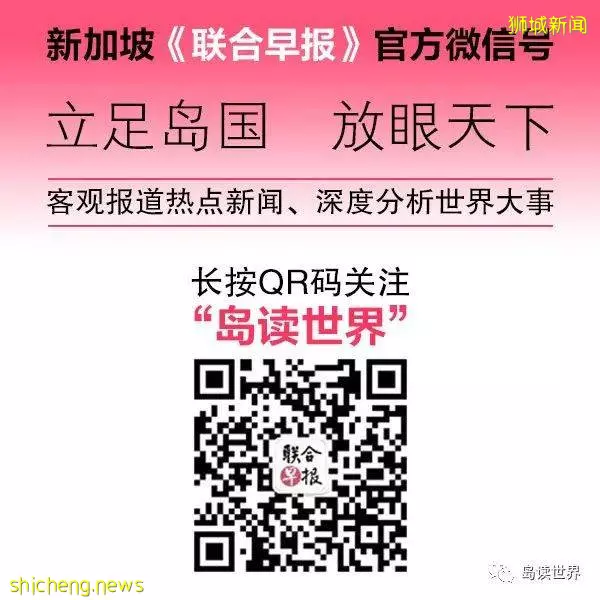亚历克管理的“伟达父子洋行”在《海峡时报》的广告列出新加坡分行在马来亚的工程,虽大多是青铜铸制的商号、栏杆、锻铁门等,不过最抢眼和具艺术价值的是他为在1939年8月3日开放、新古典主义的前新加坡最高法院操刀的工程:前门门廊横楣处的五块预制浮雕石板、主立面的三块预制石材徽章和大堂楼梯纹章的九块铸青铜框架。横楣的浮雕石板展示新加坡开埠初期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与殖民者的生活日常。1989年11月28日,读者Isabel M.Ferrie致函《海峡时报》,指出这五件浮雕的图是其父亲George Thomas Squires以他的马来司机为模特儿绘制,是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得奖作品,浮雕则由“在日据时期战亡的Alec Wagstaff雕刻。他是战前上海大名鼎鼎的雕塑家W.W. Wagstaff之子。”

亚历克为我国前最高法院(现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横楣雕刻的五件浮雕。(林方伟摄)

对照《海峡时报》广告上马来渔民的设计原图,可见亚历克的雕刻造诣。(林方伟摄)
殁于泰缅死亡铁路
二战杀到家门前,炸断了亚历克在新加坡崛起的艺术事业,人生亦草草收场,让人无限惋惜。
《马来亚论坛报》(The Malaya Tribune)12月2日报道马来亚昨日中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亚历克所属的海峡殖民地志愿部队全面被动员,说明他在12月15、16日前或许已被征召入伍,林肯路住家只留下黄逸梵,解释了她违反灯火管制的报道为何未提到亚历克。
据盟军战俘卡编号WO 345/53,亚历克在1942年2月15日被捕,关在马来亚战俘营,后来被送去修建连结泰国与缅甸仰光的铁路。长达415公里的铁路在高死亡率的代价下,17个月后于1943年10月17日完工,大部分战俘死于过劳、营养不良、虐待或霍乱、疟疾等传染病。1943年6月22日亚历克也殁于这条死亡铁路,得年36岁。亚历克(Alec)的名字在战俘记录多次误写为Alex,不过所属的单位相同,职务都为炮兵,所以肯定是同一人。

二战战俘修建泰缅铁路。(取自澳洲战争纪念网)
林肯路35号
1942年8月22及23日,《昭南新闻》刊登了一则“受命于敌方产业保管者”拍卖“伟达父子洋行”工具器材的广告,提供了几个重要的信息。林肯路35号当时已人去楼空:亚历克沦为战俘,黄逸梵早已离去,张爱玲在《对照记》与《小团圆》透露黄逸梵坐难民船逃到印度去了。从广告罗列的拍卖品,可以想像黄逸梵与亚历克居住时屋里的情况,也证实了此地是亚历克的工坊,一窥其规模:“一位雕刻家工坊所有的工具、家具和装置:包括大量不同尺寸的钢条、铸铁块、青铜板、熔炉、模具、大小铁台钳、青铜装饰品、吊灯、瓦楞锌片等。”同年9月16日,《昭南新闻》一则极小的招聘启事揭示林肯路35号已改名为“日之丸雕像”(Hinomaru Statuary),欲聘一名“有经验,能说上海话的女助手及试用员工(性别不拘)。工作提供极佳学习制造模型、制模与翻铸铜像的机会。”

1942年8月22日《昭南新闻》刊登日军拍卖伟达父子洋行工具器材的广告。(国家图书馆旧报档案)
难道亚历克的工具卖不出去,被日本人顶了下来?为何需要聘用会说上海话的女性助手?是“日之丸”当时跟亚历克父亲在上海工作室的工匠还有联系、合作吗,所以需要会说上海话的助手?
1945年9月2日日军正式投降,10月9日《海峡时报》刊登启事,“日之丸雕像”又改为“新加坡雕刻造型公司”。
1946年,丧子心碎的老威廉卖掉上海所有产业与妻子回到英国,在肯特郡Stubble Down落户至1961年。1949年,黄逸梵从南洋启程到英国,下船投靠的就是他们夫妇俩。
英联邦战争公墓委员会(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记录显示: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炮兵,编号12979,亚历克的名字于1957年2月11日刻在泰国北碧盟军战俘公墓(Kanchanaburi War Cemetery)的室内纪念碑上,以慰亡魂。亚历克从1937年到1941年的作品,随着新加坡的高度发展,拆的拆,毁的毁,庆幸的是,他与父亲或许会引以为傲的在国家法院的浮雕得以保存下来,留在如今已变身为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门楣上,让我们得以见证他在南洋最飞扬与光辉的成就。
今日,林肯路上的洋房全被摩登公寓大楼取代,黄逸梵与亚历克的前尘往事已随着35号老洋房的拆除烟消云散。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正如张爱玲所说:“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我国已故建筑师李急麟(Lee Kip Lin)摄于1992年,林肯路2号洋房。35号洋房的照片至今尚未找到。(国家图书馆PictureSG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