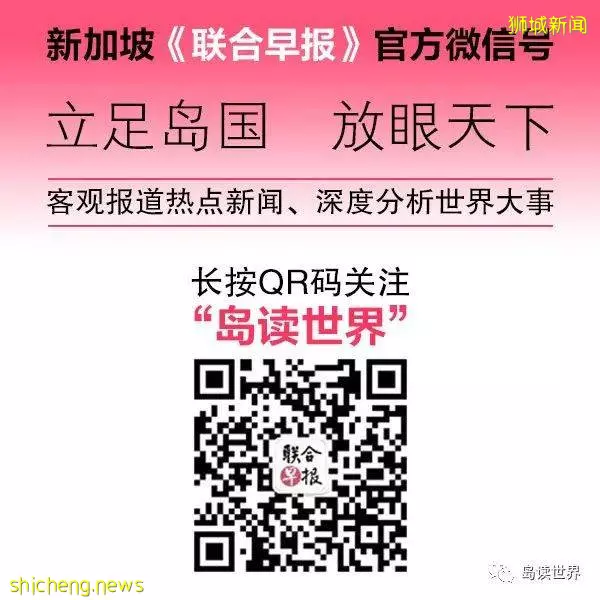亞歷克管理的「偉達父子洋行」在《海峽時報》的廣告列出新加坡分行在馬來亞的工程,雖大多是青銅鑄制的商號、欄杆、鍛鐵門等,不過最搶眼和具藝術價值的是他為在1939年8月3日開放、新古典主義的前新加坡最高法院操刀的工程:前門門廊橫楣處的五塊預製浮雕石板、主立面的三塊預製石材徽章和大堂樓梯紋章的九塊鑄青銅框架。橫楣的浮雕石板展示新加坡開埠初期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與殖民者的生活日常。1989年11月28日,讀者Isabel M.Ferrie致函《海峽時報》,指出這五件浮雕的圖是其父親George Thomas Squires以他的馬來司機為模特兒繪製,是在比賽中脫穎而出的得獎作品,浮雕則由「在日據時期戰亡的Alec Wagstaff雕刻。他是戰前上海大名鼎鼎的雕塑家W.W. Wagstaff之子。」

亞歷克為我國前最高法院(現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橫楣雕刻的五件浮雕。(林方偉攝)

對照《海峽時報》廣告上馬來漁民的設計原圖,可見亞歷克的雕刻造詣。(林方偉攝)
歿於泰緬死亡鐵路
二戰殺到家門前,炸斷了亞歷克在新加坡崛起的藝術事業,人生亦草草收場,讓人無限惋惜。
《馬來亞論壇報》(The Malaya Tribune)12月2日報道馬來亞昨日中午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亞歷克所屬的海峽殖民地誌願部隊全面被動員,說明他在12月15、16日前或許已被徵召入伍,林肯路住家只留下黃逸梵,解釋了她違反燈火管制的報道為何未提到亞歷克。
據盟軍戰俘卡編號WO 345/53,亞歷克在1942年2月15日被捕,關在馬來亞戰俘營,後來被送去修建連結泰國與緬甸仰光的鐵路。長達415公里的鐵路在高死亡率的代價下,17個月後於1943年10月17日完工,大部分戰俘死於過勞、營養不良、虐待或霍亂、瘧疾等傳染病。1943年6月22日亞歷克也歿於這條死亡鐵路,得年36歲。亞歷克(Alec)的名字在戰俘記錄多次誤寫為Alex,不過所屬的單位相同,職務都為炮兵,所以肯定是同一人。

二戰戰俘修建泰緬鐵路。(取自澳洲戰爭紀念網)
林肯路35號
1942年8月22及23日,《昭南新聞》刊登了一則「受命於敵方產業保管者」拍賣「偉達父子洋行」工具器材的廣告,提供了幾個重要的信息。林肯路35號當時已人去樓空:亞歷克淪為戰俘,黃逸梵早已離去,張愛玲在《對照記》與《小團圓》透露黃逸梵坐難民船逃到印度去了。從廣告羅列的拍賣品,可以想像黃逸梵與亞歷克居住時屋裡的情況,也證實了此地是亞歷克的工坊,一窺其規模:「一位雕刻家工坊所有的工具、家具和裝置:包括大量不同尺寸的鋼條、鑄鐵塊、青銅板、熔爐、模具、大小鐵台鉗、青銅裝飾品、吊燈、瓦楞鋅片等。」同年9月16日,《昭南新聞》一則極小的招聘啟事揭示林肯路35號已改名為「日之丸雕像」(Hinomaru Statuary),欲聘一名「有經驗,能說上海話的女助手及試用員工(性別不拘)。工作提供極佳學習製造模型、制模與翻鑄銅像的機會。」

1942年8月22日《昭南新聞》刊登日軍拍賣偉達父子洋行工具器材的廣告。(國家圖書館舊報檔案)
難道亞歷克的工具賣不出去,被日本人頂了下來?為何需要聘用會說上海話的女性助手?是「日之丸」當時跟亞歷克父親在上海工作室的工匠還有聯繫、合作嗎,所以需要會說上海話的助手?
1945年9月2日日軍正式投降,10月9日《海峽時報》刊登啟事,「日之丸雕像」又改為「新加坡雕刻造型公司」。
1946年,喪子心碎的老威廉賣掉上海所有產業與妻子回到英國,在肯特郡Stubble Down落戶至1961年。1949年,黃逸梵從南洋啟程到英國,下船投靠的就是他們夫婦倆。
大英國協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記錄顯示: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隊炮兵,編號12979,亞歷克的名字於1957年2月11日刻在泰國北碧盟軍戰俘公墓(Kanchanaburi War Cemetery)的室內紀念碑上,以慰亡魂。亞歷克從1937年到1941年的作品,隨著新加坡的高度發展,拆的拆,毀的毀,慶幸的是,他與父親或許會引以為傲的在國家法院的浮雕得以保存下來,留在如今已變身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門楣上,讓我們得以見證他在南洋最飛揚與光輝的成就。
今日,林肯路上的洋房全被摩登公寓大樓取代,黃逸梵與亞歷克的前塵往事已隨著35號老洋房的拆除煙消雲散。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正如張愛玲所說:「故事還沒完,完不了。」

我國已故建築師李急麟(Lee Kip Lin)攝於1992年,林肯路2號洋房。35號洋房的照片至今尚未找到。(國家圖書館PictureSG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