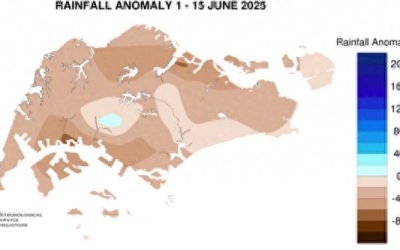李光耀希望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他深信,中国若发生政治内爆,将给全世界带来可怕的风险,其中的各种危险在苏联解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李光耀后来对比中苏两个案例时说:
邓小平是中国唯一在政治上有权威,也有力量扭转毛泽东政策的领导人……
邓小平经历过革命,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不同,他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革命,没有看出苏联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再次启动。在那次长达一个月的影响深远的重要旅行中,名义上已经退休的87岁的邓小平走了好几个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周旋于中美之间
对美国来说,李光耀关于中国的评论令它清醒,其最深层的意思听之逆耳,即:美国在西太平洋,也许在更大的世界中,将不得不与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共处”,李光耀在2011年说,而这“对美国是全新的感受,因为以前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而中国在20~30年后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说,这样的形势对坚信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社会来说将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繁荣本身就源于例外因素:“地缘政治的好运、丰富的资源和大批移民带来的活力、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把美国与世界冲突远远隔开的两个大洋。”在今后的世界里,随着中国成为拥有尖端技术的可畏的军事强国,地理不再是美国的屏障。
李光耀预见到,将要到来的变化会对现有国际平衡构成挑战,使夹在中间的国家难以自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告诫李光耀说:“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们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欢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尔说:“大象做爱,小草也遭殃。”
他相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静的关系,那将最有利于新加坡的稳定与增长。但是,李光耀在与华盛顿和北京的互动中,表现得不像新加坡国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两个可怕巨人的哲学导师。
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李光耀一般会从切合中国苦难历史的角度组织论点,言谈间带着他在其他场合鲜少表露的感情。2009年,他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告诫,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他们的前辈遭遇的贫困和灾难,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深感不满:
这(老的)一代有着惨痛的经历,经历过“大跃进”,挨过饿,几乎饿死,差点儿与苏联人发生冲突……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我毫不怀疑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们的孙辈呢?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了。如果他们开始展示肌肉,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孙子从来不听爷爷的话。
另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世界一直亏待你,认为世界剥削了你,帝国主义者摧毁了你,抢劫了北京,对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这样是不行的……你已经回不到中国曾是世界唯一强国的往昔了……现在,你只是许多强国中的一个,而很多其他强国比你更善于发明创造,更顽强坚韧。
反过来,李光耀也劝美国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敌人”,除非它“发展出要在亚太地区推翻美国的战略”。他警告说,事实上,中国人可能已经在设想这样的场景了,但难以避免的“两国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争……并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因此,李光耀建议华盛顿让北京融入国际社会,并接受“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国家”,“在董事会会议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国不应让中国人将它视为敌人,而应“承认(中国)为大国,为它重获尊敬、重拾昔日辉煌而喝彩,并建议具体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认为尼克森政府实施的就是这种方针,称尼克森总统为“务实的战略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应采取“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姿态,不过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要悄悄地做好后手准备,以防中国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样遵守规则”。这样,万一本地区国家感到不得不“选边站,那么棋盘上美国一边应该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两岸阐述观点时我都在场。与他对话的美国人总的来说同意他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会询问他对于当下问题的看法,例如朝鲜的核方案或亚洲各经济体的表现。美国人也满怀期望,希望中国最终能采纳与美国相近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与李光耀对话的中国人欢迎他关于中国应得到大国待遇的论点,也同意,即使从长远来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冲突。但是,在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之下,可以感觉到他们听一个海外华人指点中国应遵循何种行为原则,内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将是世界末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定会造成毁灭。除了毁灭,谈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战争目标,尤其无法界定何为“胜利”。所以,对从未经历过他同代人的颠沛流离,可能过于依赖技术或实力的那一代中国人,李光耀晚年坚持发出呼吁并非偶然:
中国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国的和平与增长期,没有经历过中国过去的动乱。必须使他们了解中国因骄傲自大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让他们以谦卑和负责任的态度迎接未来。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对话方,全球化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包括(也许特别是)创立了这个制度、书写了它的规则的国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生活。
他在世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全球化终于定型。在这样的世界里,极大的繁荣与严重的匮乏比邻存在,必将激发爆炸性情绪。“地区主义不再是终极解决办法,”李光耀在1979年说,“互相依存是现实。全球同属一个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当,全球互联会造福所有人。
如李光耀在2002年对我说的,毕竟新加坡与世界的融合是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冷战的结束产生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美中之间潜在的战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有导致灾难性战争的风险。许多人只看到了危险,李光耀却坚持力行克制的必要性。美国和中国都负有至关重要的义务,必须对两国关系的成功注入希望并为此采取行动。
只有李光耀早早地预见到了中国的发展给中美两国带来的两难困境。两国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不可避免。这种新关系会加剧它们的对抗吗?还是它们有可能放弃敌对行为,转而一道分析和平共处所需的条件?
几十年来,华盛顿和北京都宣称后者是自己的目标。但是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今天,两国似乎中止了对共存的追求,转向日益激烈的竞争。世界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段时间一样滑向冲突吗?当时,欧洲外交无意中成了推动世界末日的机器,令一个接一个危机越来越难以解决,直至最后引发大爆炸,将当时所认知的文明炸得粉身碎骨。还是说美中这两个巨人会找到共存的新定义,一个对它们各自关于自身伟大和本国核心利益的认知都有意义的新定义?现代世界的命运寄托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之上。 李光耀见解深刻,成就卓著,是少数几位在太平洋两岸都受到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他为一个蕞尔小岛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出了秩序概念。到了晚年,他力劝有能力造成全球大灾难的国家明智而为,力行克制。李光耀本人决不会如此自诩,但是这位现实主义老人担当了“世界良知”的角色。
李光耀的遗产
1990年11月,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结束了他漫长的任期。为确保过渡稳定有序,他一点点地从国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来。他辞去总理一职后,先担任高级部长,然后又担任内阁资政,在随后的两届总理任期中依然保留着影响力,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
评价李光耀的遗产要先从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非凡增长说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长到1.19万美元,2020年达到了6万美元。GDP平均年增长率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现代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普遍认为前殖民地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本国经济免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并通过国家大力干预来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为了表现新获得的解放,有些这样的领导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冲动的刺激下,甚至认为必须让殖民时期在本国土地上落户的外国人过不安生。这样做的结果正如理察·尼克森所写:
当今时代,评判领导人常常是看他们言辞的尖锐和政治的色彩,而不是他们政策的成功。特别是在发展中世界,太多的人白天听了一耳朵话,夜里睡觉却空着肚子。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拥抱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坚持严格履行商业合同,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他珍视新加坡的民族多样性,将其视为特殊的资产,不遗余力地防止外部势力干预国内争端,因而帮助维护了国家独立。
在为他的新社会确定路线的时候,李光耀高度重视文化的中心作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所有社会实现现代化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李光耀拒绝接受这个观念,恰恰相反,他说:“西方相信世界必然追随(它的)历史发展。(但是)民主和个人权利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陌生的概念。”他无法相信自由主义主张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他难以想像美国人有一天会选择追随孔老夫子。
但是,李光耀同样不相信这种文明差异无法逾越。不同文化应共存互容。今天,新加坡依然是威权国家,但威权主义本身并非李光耀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家族专制同样不是目的。吴作栋(和吴庆瑞没有亲戚关系)从1990年11月到2004年8月担任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的能力无人质疑,他继吴作栋之后担任总理,现在正逐渐从总理职责中抽身。他的继任者将由下一次大选决定。新加坡在这两位总理的先后领导下,沿着李光耀确定的道路继续前行。
新加坡的选举不民主,但并非没有意义。在民主政体中,民众通过选举换人来表达不满。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继任者使用投票作为一种业绩评比,让当权者藉以了解自己行动的效力,因此让他们有机会根据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来调整政策。
有没有另外的办法呢?另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多元的做法有可能成功吗?李光耀认为不会。他相信,新加坡最初走向独立之时,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一样,面临着被派别势力撕裂的危险。在他看来,存在严重族裔分歧的民主国家可能会沦入身份政治,而这又会加剧派别主义。 民主制度的运作意味着多数人(对这个词的定义五花八门)通过选举建立政府,当政治意见发生转变时再选举另一个政府。但是,如果决定政治意见以及政治分歧的是身份定义这个不可变因素,而不是易于变化的政策差异,那么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可能性便依照分歧的程度成反比下降。多数派会永远占上风,少数派则企图通过暴力摆脱自己被压制的状态。 李光耀认为,由一群关系密切的同僚组成务实的机构,不受意识形态制约,重视技术与行政能力,不懈追求卓越——这样的机构开展治理最为有效。他的试金石是公共服务意识:
政治对一个人有特别的要求,必须忠于人民和理想。你不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种召唤,和担任神职不无相似之处。你必须感人民之所感,必须立志改变社会,改善人民生活。
明天会如何呢? 就新加坡的未来而言,关键问题是持续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向着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会过渡。这个国家的表现若是不如人意,因而导致选民寻求族裔身份的保护,那么新加坡式的选举就可能变质,成为一党独大的种族统治的证明。
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测试一个结构要看它能否达到固定的标准;对政治家来说,要看它适应历史环境的能力。根据后者的标准,李光耀的遗产迄今为止是成功的。但是,政治家也必须经受他们所创立模式的演变结果的评判。对民意变化的容许程度早晚会成为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义之间能否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将是新加坡面对的终极挑战。
如同新加坡刚刚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时期。关于如何建立成功的社会难有定论。苏联解体后,自由市场民主自称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却同时面临着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现和内部民众信心的减退。其他的社会制度宣称自己能更好地释放经济增长,培育社会和谐。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转变中避开了这种斗争。李光耀对被他贬为“宠物理论”的僵硬教条避之不及。他一手设计了他所坚称的新加坡例外主义。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论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势需要随机应变。他采取他认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发现并不有效,就马上修改。李光耀总是在试验各种办法,学习其他国家的好主意,也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从来不迷信别国。相反,新加坡必须不断自问,它是否正在实现由它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并由它特殊的人口组成所推动的目标。 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受任何理论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现实。我测试每一种理论或科学的决定性标准是,它管不管用?”可能柯玉芝教给了他亚历山大·蒲柏的格言:“争论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创造了一个民族,还确立了一个国家模式。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构想出了一个民族,然后千方百计鼓励他的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出色发挥,实现发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断创造变成了习惯。此法能够适用于不断演进的人的尊严的概念吗?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说,人“没有本质,他拥有的是……历史”。在缺乏国家历史的情况下,李光耀根据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发明了新加坡的本质,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书写了新加坡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李光耀展示了他的信念的中肯,即政治家的终极考验是他在“沿着没有路标的路走向未知目的地”的途中如何运用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