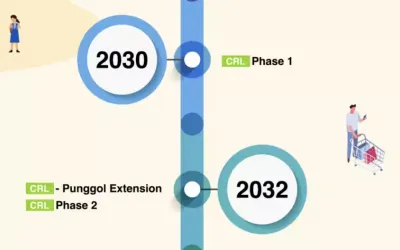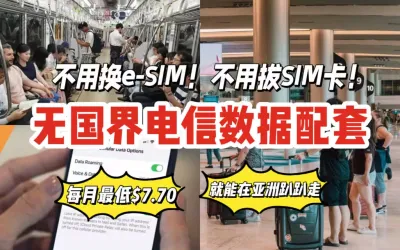另一方面,由于新加坡本身已成为一处国际美食天堂,所以这里的阿拉伯人很难像在西方国家的阿拉伯移民那样在家园以外推广自己的传统菜肴。他们中也很少有人讲阿拉伯语了,除去一些可爱的传统,比如仍会称呼女人为sharifa——意思是“高贵”。
家系和宗教是他们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很多家族的家系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本·伊萨·阿尔·穆哈吉尔(Mohamad bin Isa Al Muhajir),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10代后裔,在公元956年离开巴格达搬到哈德拉毛。现在,社区里的大部分家庭会在每周五晚聚在一起,帮助孩子学习宗教知识。

伊玛目·哈桑·阿尔-阿塔斯(Imam Hassan Al-Attas)出身于一个精神领袖世家。他和妻子与他们的大家族生活在一起。在家中吃晚饭时,他与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聊起了祖先的历史和信仰。“很多人说,哈德拉毛人来这里是传播伊斯兰教的,但当然,大多数人不是这样,”阿拉塔斯说。“推动因素有很多,比如生活不稳定、内战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饥荒。”
“一千年前,哈德拉毛非常富饶。但是,近500年来,那里变得越来越贫瘠。所以人们开始外出找工作,养活自己。因为哈德拉毛的教育基本上以宗教为主,他们或许是商人,或许是业主,但当他们走出去,到其他国家找工作的时候,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改变了当地的人,特别是通过联姻。”
“同时,也来了些真正的学者,”伊玛目·哈桑补充道。他自己的家族就是个鲜活的例子。“随着社群的不断壮大,他们应邀来这儿担任某些职位。他们有时也会扮演多重角色——你是一名传教士,但也需要通过经商获得经济支持。”
伊玛目·哈桑和阿拉塔斯说,与其他因素相比,新加坡的中东式街道名称与它的战略位置关系更大。正如新加坡是贸易中心一样,这里也是各地朝圣者的补给点。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东方其他地方的朝圣者会在这里进行物资补充,然后继续麦加朝圣之旅。

哈桑提到,在政府通过监管资金并根据邻近人口签发建筑许可证的方式合理规划清真寺的建造之前,他的父亲就已经于1952年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清真寺。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新加坡发生了太多的变化,”他说。“他有三份护照——英国的,马来西亚的,然后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后,他又拿到了新加坡护照。唯一不变的是他的哈德拉毛人身份。我仍然记得,我父亲在布道的时候说的是阿拉伯语。人群中也有马来人,特别是星期五祷告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懂阿拉伯语。”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穆斯林宗教协会(Muslim Religious Council)成立后,所有穆斯林劳动者每个月都会自动从工资里捐出一新元,用来支援清真寺的建设。“当收集到足够的资金时,政府就会替一个穆斯林社区把钱交给宗教协会,有可能是印度社区也可能是马来社区,帮助他们建设自己的清真寺。”伊玛目·哈桑说。“以前,有些清真寺是木结构的。现在经过重建,这些清真寺变得更漂亮了,也装上了各种现代设施。”
新加坡几乎所有的事物都非常时髦,就连较陈旧的也不例外。像阿拉伯人聚居区这样的民族聚居区也很整洁有序,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从早到晚迎来各种各样的游客,但原住民的后裔们大多住在其他地方,在时尚新加坡那闪亮的高塔间,在清新自然、绿树成荫的街道和花园间。
他们在各行各业工作,有教授、外交官、银行家、作家、秘书,偶尔还有开商店屋的老板,他们共同交织成这个国家的商业图景。他们一边惬意地行走在乌节路(Orchard Road)和其他整洁的大道上,或在滨海湾(Marina Bay)附近悠然散步——这里的鱼尾狮(一半狮子一半美人鱼)雕像是本城的吉祥物,也是一个旅游景点——一边倾听着阿拉伯街的唤礼辞。
“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像新加坡这样了,”卡勒德·塔利卜说,他对新加坡人的复杂性作出了总结。“我以前在阿联住过一年,尝试加入一个新加坡俱乐部。我打电话给俱乐部的负责人,那人是个华人,他不相信我是从新加坡来的。你可以看到,他对新加坡人的视角就和我不一样。所以我喜欢说自己是在新加坡出生的阿拉伯人,马来人的暂住客,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的原始主人。”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做些哈尔瓦甜食(halwa)和小麦粉布丁(muhalabiyyah)当作点心。有些事情并没有改变。”

艾莉雅·尤尼斯艾莉雅·尤尼斯(www.aliayunis.com)是一位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现居阿布扎比。她撰写的小说《夜晚计数器》(The Night Counter)(兰登书屋,2010年)广受读者好评。This article appeared on page 38 of the print edition of Saudi Aramco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