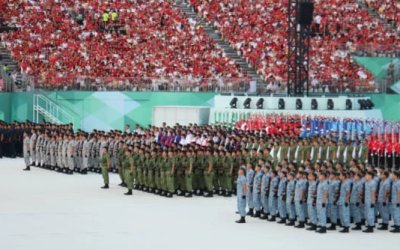哈斯:就像我们在地球另一端常说的:“因沙拉!”(但凭真主之意)如果问起人们 说到词汇联想,说起“全球化”,跟全球化联想到一起的国家,新加坡……
李显龙:我们名列前茅
哈斯:没错,但现在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词是 “去全球化”,因为有制裁、有约束和央行资产被冻结,因为供应链、冠病和中美摩擦等因素。您对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之间的这种平衡有什么看法?您又有什么担忧?
21:02 -【平衡 “全球化” 与 “去全球化”】
李显龙:对我们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平坦的世界里。政治评论家汤姆·弗里德曼以前经常写这样的书,但这世界并不平坦,不仅有丘陵和山谷,还有不易跨越的鸿沟,有些甚至正在加深。我们必须尽可能属于这个世界,最大最平坦最安全的部分,以确保我们能继续维持生计。
我无法预见任何国家走回头路,完全回归到各自为政。要完全只在美国制造苹果手机是不可能的,就像要完全只在美国制造波音飞机一样。国际贸易是有必要的,商业往来也是必须的。我们要有程序,才能确保我们能信赖合作伙伴,同时可以互相依靠,并在出现问题时有冗余保障,但国际间的相互依存和经济合作仍必须继续进行。
这其中也存在挑战,那就是要如何讨论重新塑造和重建美国制造业等善意的举措,却又不使这些举措被过度渲染,而成为不赚钱经济活动的代名词。这会导致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美国工人陷入困境,这就是美国所面对的挑战。
对我们而言,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确保我们仍是可靠的全球供应链的一分子,继续和你们合作,维持良好关系。而你们也能继续信任我们,继续保持商务往来,不光是新美两国,而是有个可发挥“墨迹扩散”效应的更大框架,让更多的国家相互合作,而对那些框架之外的国家,有某种筛选形式,而不是完全把他们排除在外。
因为我认为,如果说你们要和中国切断一切关系,你不但不会打倒它,反而会严重地伤了自己。
哈斯:我同意您的观点。有时候,我更喜欢“保持距离”这一词,倾向于选择性地保持距离 而不是完全切断关系。在联合声明中有一部分——我们稍后会再接受各位的提问——有关朝鲜的部分,提到大家都熟悉的概念: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持有乐观心态,但我认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永久和平机制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么,您认为实际可行的进程是什么?如果无法实现 即便是个长期目标,您认为在朝鲜问题上,实际可行的短中期目标又是什么?
李显龙:谁的目标?
24:00 -【朝鲜半岛局势】
李显龙:我认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我不认为会有哪些政治人物同意朝鲜应该拥有核武器.我觉得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朝鲜会面临吓阻,现状得以维持,但很多国家还是会继续不承认朝鲜,因为一旦承认了,就会造成许多后果。每个人的直接反应将是,既然它有权拥有核武器,还能受他国承认,那我呢?我为何不采取行动?如果朝鲜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却拥有,那就应该受到遏制,这或许能防止核武器继续进一步扩散,这是有可能。
哈斯:但与此同时,我知道您想说的是……
李显龙:我不认为朝鲜的做法是疯子的行为,他们看到的是,核武器有很大的威慑作用,所以他们势必不会放弃,无论是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政权。
哈斯:您一开始其实就提到这一点。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不管这是不是其中一个预料之外的结果,《布达佩斯备忘录》 给予乌克兰安全保障,乌克兰也归还了从苏联继承下来的核武器。但如今,乌克兰已遭受两次侵略,2014年和现在;萨达姆和卡扎菲政权也已瓦解成为历史。您是否担心,尽管我们都反对核武器的扩散,但外交政策的很多层面似乎在支持核武扩散?
李显龙:我们对此确实感到担忧,但这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
哈斯:在这严肃的基调上,容我开放让观众提问,拿到麦克风后,请道明身份。我可能会来点羽毛球或桌球之类的玩法,或是匹克球——考虑到在场观众的年龄——我们在观众之间来回进行。
李显龙:可别忘了演讲者。
哈斯:有道理,您说得对。萨克海姆,请。
多福·萨克海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理先生,很高兴再次见到您。上次和您见面的时候,我的头发比现在茂密得多。想请问您关于南中国海局势,以及您是否认为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与您所谈到的分裂以及其后果,将对南中国海的局势产生任何影响?换句话说,认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会是如何?现状是否持续?或者可会有任何变化?
27:31 -【南中国海纷争】
李显龙:我认为南中国海存在着一些事实。各个环礁和岛屿由不同的国家占据。有的填海造地、扩大岛礁、筑防御基地,主权声索相互重叠,错综复杂。中国是主权声索国,东盟其中四国也是,不包括新加坡。
东盟和中国一直在进行长期对话,探讨如何处理问题。我们有个《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也正在商议拟定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守则。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我们也有了谈判文案,我们拟定了序言部分,但制定行为守则非常困难,因为要定义问题,就已经是在问题上纠缠了。具争议性的部分是哪些?我的部分可没有争议,你的才有争议。因此,我认为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我们看来,航行自由是重要的,国际法是重要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重要的,而和平解决争端也是重要的。这样才能避免一些有可能升级的意外冲突或碰撞。
我并不认为声索国会想看到问题走向极端,因为东盟所有国家都和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而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虽然非常重要,但这只是宏观层面的其中一个问题。
因此我认为可以作出一些妥协。我们关注的是航行自由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因为大量的国际贸易都需要经过南中国海,如能源和许多其他物资。说回乌克兰,我认为南中国海问题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我不认为这与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有何密切关联。
麦可·莫塞蒂希(PBS Online 新闻一小时):贵国外长呼吁积极调解,并提议邀请中国来当乌克兰局势的调解者。中国真能充当独立的调解人吗?考虑到中俄关系正日益密切,许多观察者也认为,确保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不至于太难堪,其实攸关中国的实际利益。
李显龙:我觉得你是在引述彭博社报道的一个标题。这篇报道渲染了我国外长的讲话,我并不认为他是这个意思。
30:32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充当协调人?】
李显龙:我也不认为中方会自愿扛起这项任务。我认为,他们会宁可由其他人出面,而我也不认为缺乏调解人是乌克兰局势的问题所在。
史蒂芬·比根(Macro Advisory Partners LLC):新加坡是亚洲其中几个重要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但印太地区也有许多其他组织,甚至是新的组织,例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不算太新的组织,但肯定在演变,还有五眼联盟,也不是什么新机制,但是个重要平台。
总理先生,我只是想了解新加坡的看法。您是否支持这些组织,尤其是新冒起的组织?您怎么看新加坡的角色?未必是加入,而是您如何看待与它们的关系?
31:40 -【新加坡如何看待全球安全安排】
李显龙:我们理解这些新组织成立的原因。美国在本区域有其战略利益,并希望推进这些利益,而美国自然会想要与不同国家组建各个组织,以实现共同目标。AUKUS是个例子,四方安全对话是另一个,五眼联盟存在很长时间了,而这些组织都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环。
东盟仍然处在这个格局中。我们谈论过东盟的核心地位,而如果东盟能够凝聚各方力量,扮演有用的角色、促成讨论、召集各方,那么其他各方也都会有各自的位置。但这得取决于东盟。东盟有10个不同国家,地缘政治情况和战略观点各异。
所以想让东盟取得共识并发挥影响力,需要一个过程。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东南亚地区必须拥有一个轴心点来聚拢各成员国,而不是把彼此推开。
此外,还有其他因素把东盟各国凝聚起来。我刚才提到亚太经合组织,还有东亚峰会,这与东盟有着密切关系,与会国包括俄罗斯、中国、美国和印度,另有印太经济框架。我们希望当这个框架成立后,有朝一日至少会是个具包容性的组织。当你有了这些具包容性的组织,当然其他组织也能存在,这就是世界的规律。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总理先生,我曾好长一段时间在新加坡担任财经记者,很高兴再次见到您。海峡时报指数似乎已从冠病疫情的低谷中强力回弹,就像许多西方国家的情况一样,但中国股市包括大陆和香港并非如此。您是否认为接下来,新加坡至少在金融方面,因为更能与中国市场的困难处境区别开来而有所获益?
李显龙:不,我们怎么可能脱离中国市场?
蒂姆·菲格森(财经记者):或者说 与他们的区别更明显会对你们更有利吗?
李显龙:我们和中国市场不脱离 。我们有商业往来,他们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新加坡有投资,而我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投资也不少,我们希望他们好。
34:27 -【后冠病经济复苏与中国市场前景】
李显龙:许多分析师谈到中国股市下跌的原因,都归咎于政策,中国政府的决策。我认为中国想要在科技领域建立一套新规则,而他们认为股市表现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就经济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尽管受疫情冲击,中国的经济表现仍相当强劲。如果把眼光放远至后冠病时代,我们相信中国是有潜力,继续是个充满机遇、发展中的经济体。我们希望能继续和他们合作。
香港是另一个特殊情况,因为他们正处于过渡期。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市场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也因为香港自身的具体情况和条件,也需要时间化解。我们希望他们能解决。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因为香港的种种问题,一些当地的企业或民众可能希望移到别处发展,他们可能想到新加坡来,如果他们想来,我们会乐意接受。
但从更广的角度看,香港萎靡不振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宁愿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一荣俱荣,我们能生存,他们也一样,这并非是二选一的情况。
哈斯:我想就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再谈一谈。在美国的外交机构,或者甚至更广的层面来看,大家形成一种普遍的判断,经过数十年努力,仍无法成功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假设美国的希望是让中国的经济更开放,更符合国际规则,政治上更开放,在外交政策方面也不那么强势。但实际情况是,中国选择以自身的方式参与并变得更强大,姿态和行为上却并未变得更温和,而这也导致大家认为 我们需要设定更多的限制。您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正确的教训,还是过度解读了?
37:01 -【中国与全球体系】
李显龙:我想我们必须整体来看这个问题。中国要发展和壮大,我想这股崛起的动能势不可挡。问题是如何将其纳入全球体系?您可以尝试阻止它,拖延它的进度,这样你也许可以稍微自我保护一阵,但长期下来反而会让双边关系变得棘手。或者,你可以尝试与他们合作,协助他们融入全球体系,他们从中受益,你也可以得益。长久下来,你希望有个建设性的进程会发生。
我并不认为原本的预计是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这也不是我们促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或在多方面和中国接触的原因。而是因为这么做本身有好处,美国的经济、消费者、跨国公司,都因为你们与中国合作而大大获益。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认为,中国获益了壮大了,你们也获益了,企业也蒸蒸日上,没什么需要改进的。
的确,双方都得利了,可是如今平衡点已转移。过去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 ,如今它在某些领域已发展到和美国一样大,甚至可能更强大,论购买力平价 (PPP) 的话。
过去在政治或经济上可做的调整和优惠,如今已不可行,就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你们必须根据情势调整。
首先,需要逐渐将中国视为一个不再只是发展中的国家,而是越来越接近发达的经济体。其次,我们需要给它一些空间,让它可以对国际体系发挥影响。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持有股份,或对世界银行发挥影响力,你不需要改变现有的整个国际秩序体系或国际规则。这是大家都已经融入的框架,但现在来了个大国它想要参与,你必须让他们参与。
而如果你拒绝,他们会说:好吧,我大可自己来,我既然没法加入世界银行、拥有更大的投票权,那我就另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会有很多国家想加入。我也会希望和邻国合作,共同开展 “一带一路” 倡议。
原则上,这些都是合乎情理的事,因为这是个大国,你会想和它合作,而双赢的机制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会带来什么困难?困难就在于,当一个非常强大的伙伴和一个非常弱小的伙伴合作,他们将很难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
一个大国很难意识到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多大,即使它并没有这样的用意。而小国要在众多的合作项目与机遇中运行并获益,还要不时接受对方的提议或无法拒绝的要求,这也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