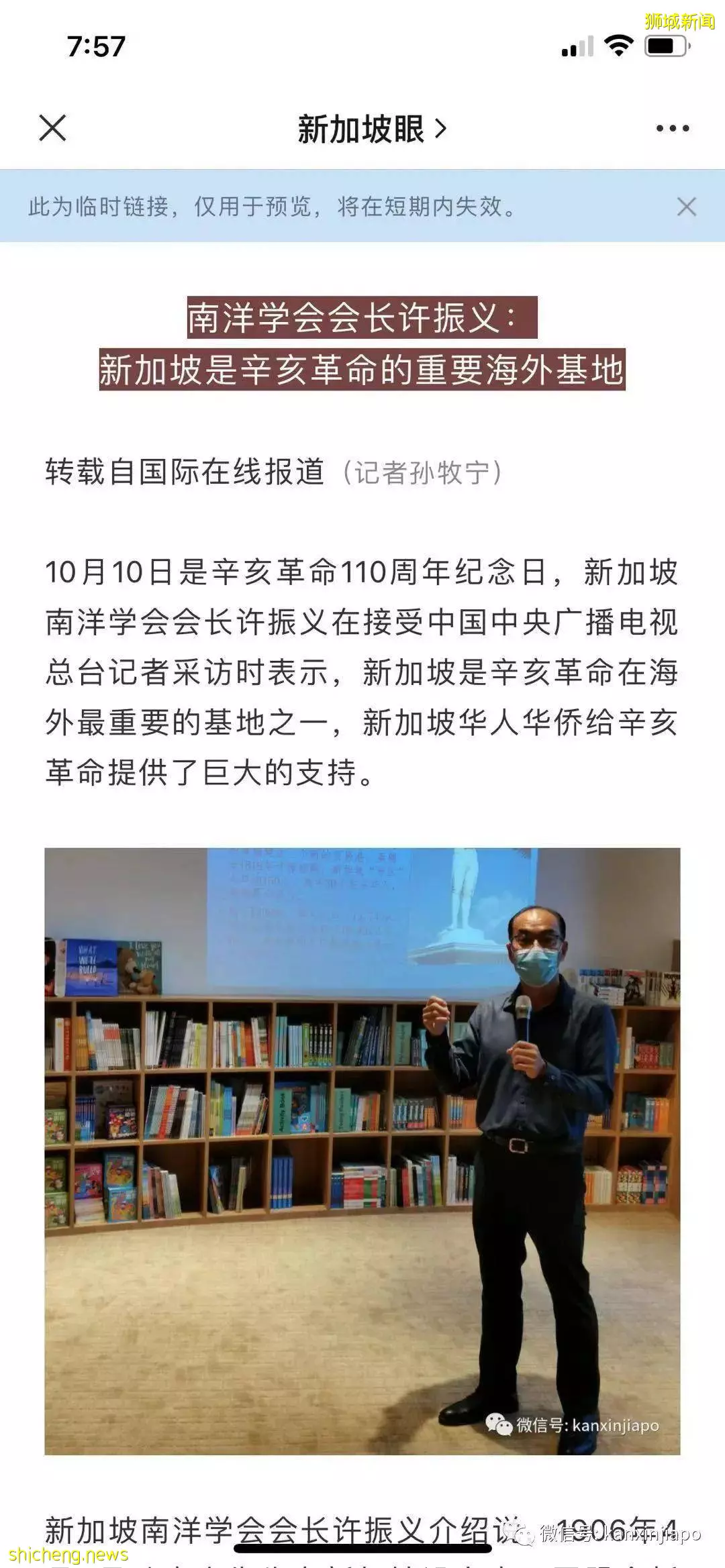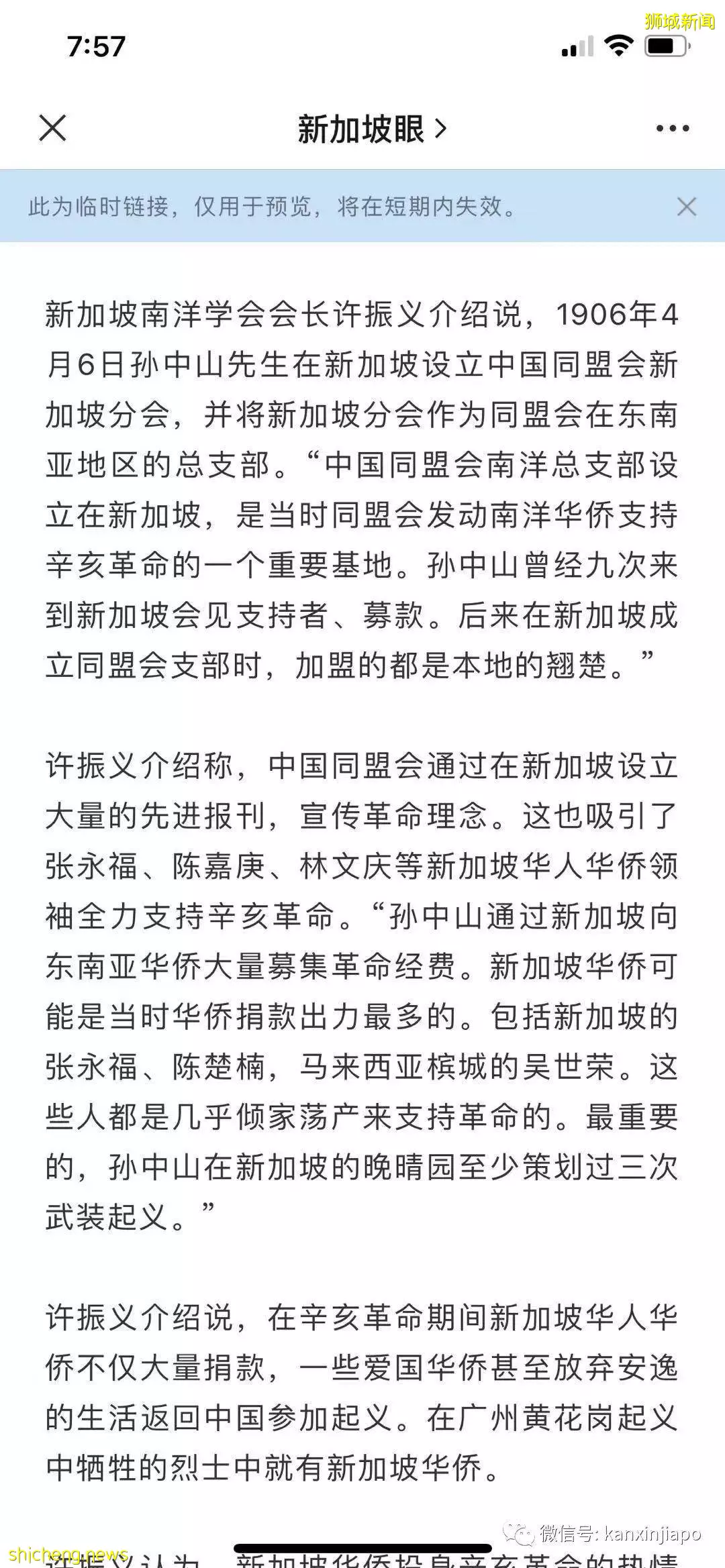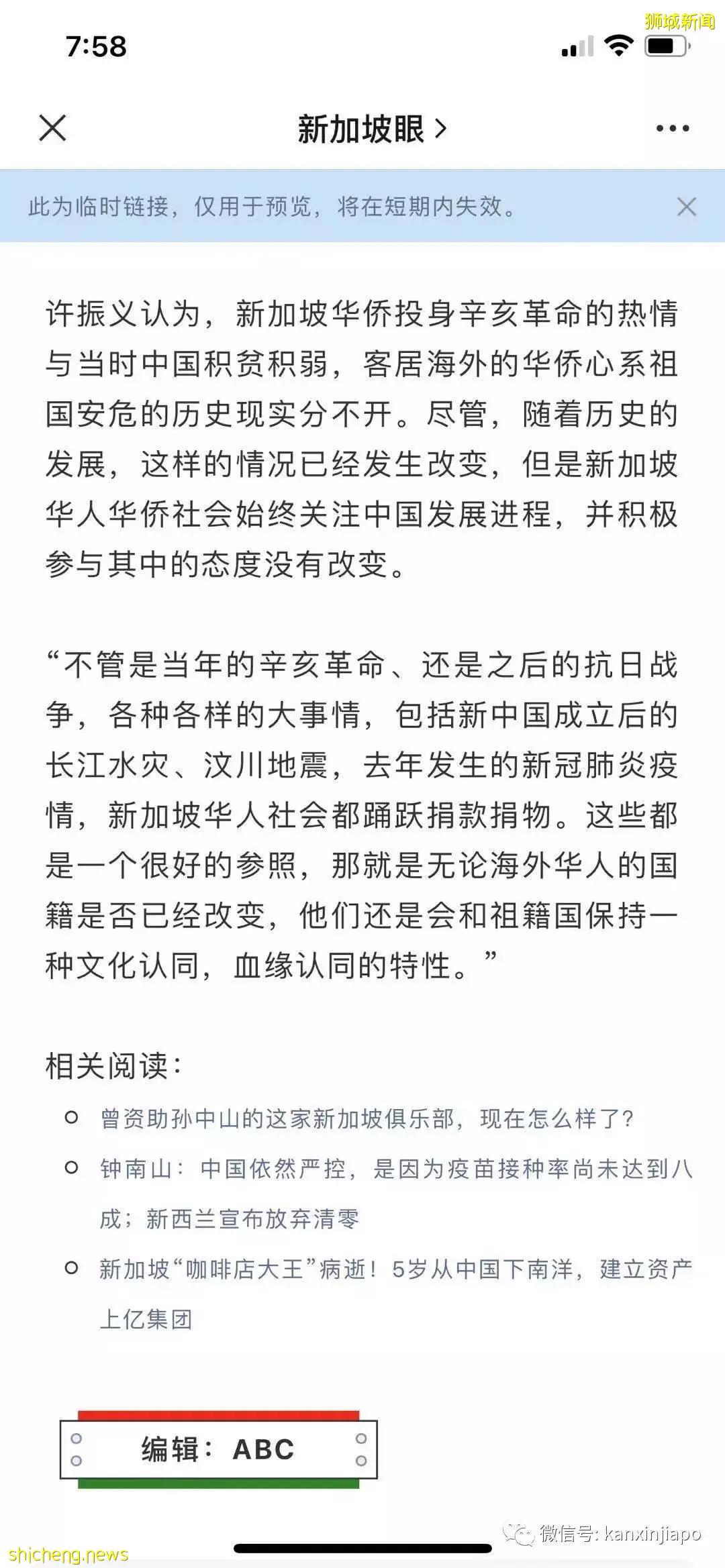这封没有署年份的电文密奏(影印本),目前保存在晚晴园。参照海峡殖民地档案,孙中山此次抵新时间应该是1908年1月27日。此密奏的结果,虽然没有促使孙中山被驱逐出境,但孙中山旅新期间的言行举止受到清廷的监视,是毫无疑问的。
孙中山的另一挑战者是康有为。 戊戌政变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七次进出新加坡鼓吹维新和保皇思想。康有为的到来,几乎与孙中山同时,都是在1900年。
邱菽园是康有为的主要支持者。邱菽园是富商,曾独资创办《天南新报》,兼任主编,并经常亲撰社论,鼓吹维新救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邱菽园捐献叻币25万元资助保皇党在汉口发动的起义。但因康有为扣压捐款,汉口起义改期数次而失败,他得知实情后大为震怒,在《天南新报》上撰文宣告,从此与康有为绝交。
此后邱菽园因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与一些革命派人士颇有私交,但对孙中山始终没有什么好感, 既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仍然为文攻击孙中山。
孙中山和康有为两人在这里的活动,引发了本地华人社会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启蒙并扩大海外华人对祖国政治参与的机会”。特别是在这两股政治力量相互竞争,彼此对立而致内部分裂的同时,也促使本地华人群体政治化的过程,“从而形塑了海外华人中华民族主义的认同”,对新马华人社会的政治思潮产生深刻的影响。
然而,甲午战败却使康有为的维新运动, 一下子没有了市场。海外华人成了“革命之母”。一度作为孙中山在新加坡及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园,在中国大历史变革中之占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战败之赐! 还有,海殖民地政府对孙中山的态度亦至关重要。当年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因此,海峡殖民地总督的行动代表了伦敦殖民部或外交部的政策。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高级讲师李励图,利用英国殖民部、外交部档案,分析两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对孙中山的态度,颇有参考价值。
李励图认为,海峡殖民地政府对孙中山的出现,在政策上曾予有限度的容忍。这表示海峡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国改革者,但却不能接受孙中山利用海峡殖民地作为其革命事业的基地,引致华人团体的不满,及干扰海峡殖民地的和平与稳定。至于英国殖民部与外交部,虽然并非完全同意各任海峡殖民政府总督在处理孙中山之事件上所作的一切决定,但他们与海峡殖民地政府的决定并无冲突之处。
孙中山旅新期间,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和约翰安德森(Sir John Anderson)为时任海峡殖民地的代总督和总督。他们有独立行动的特权,因此这二人对孙中山政策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仅是其个人判断,也代表英国的态度。
两位海峡殖民地总督对孙中山的处理手法,前后如出一辙:只要孙中山不在海峡殖民地引起骚动,他是可以居留在新加坡的。然而,一旦有确切证据,显示孙中山利用这里作为推翻满清的行动,危及英政府与北京之间的关系时,就不受海峡殖民地所欢迎,必须离去。
1910年11月1日,安德森从《槟城新报》(Penang Sin Pao)获知孙中山“在槟城的一个华人会社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激励听众支持革命,推翻满清”。此演说成为驱逐孙中山出境的证据。1910年12月7日,孙中山化名为锺蓝(Chung Lan),以二等舱旅客的身份,搭乘德国轮船离开。
新加坡辛亥人物 所谓“辛亥人物“,指的是1900至1911年,曾经与孙中山有过某种形式接触的新加坡历史名人。
孙中山旅新期间所接触的辛亥人物,除上所述外,以下三人值得一书。他们都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仍与国民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其中尤以陈嘉庚的表现最为突出:
陈武烈
陈武烈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县(今福建省龙海市海澄镇仓头村尤墩社)。从1897年到1916年,陈武烈是新加坡华社最高领导机构天福宫的主要领导人。当他中选为天福宫大董事时,《叻报》称其为“年少英才”,而《星报》则为“英才卓荦”。陈武烈也是同盟会会员,主张革命倒清,为孙中山的挚友。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1年11月,福建保安捐发动时,陈武烈被举为第一次大会临时主席,天福宫一度成了保安捐的司令部。此次为时十个月的爱省运动,共募得叻币12万元。
1911年12月15日,孙中山途经新加坡,回南京就任大总统,就下榻于“金钟大厦”(陈武烈的豪华别墅)。1913年,当国民党在新加坡选举百余位职员时,陈武烈与林义顺中选为副部长。 陈武烈领导的天福宫结束于1916年。此后有关他的资料极少,直到1934年10月17日,我们才从《星洲日报》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当年报载他于“两年前返国”(即1932年)回到中国,在中国患脑出血症逝世,终年60岁,遗体火化后运回新加坡安葬。逝世时最后职衔为侨务委员会委员。
林文庆
祖籍福建省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鳌冠,他曾任新加坡立法议会华人议员、市政府委员、内务部顾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年轻时获颁英女皇奖学金,前往英国攻读医科,学成后返新行医,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林文庆既是学者,又是教育家;亦涉足树胶业,于当地政治活动多有参与,并获封太平局绅;既推动社会风俗改革,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一生多姿多彩,在辛亥革命史上和新加坡华人史上,都留下他的身影。
林文庆关心中国形势,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带头剪掉辫子,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吸食鸦片,在当时华侨社会中引起激烈的争论。1900年,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到新加坡被捕,经林文庆向英当局疏通,使宫崎寅藏得以获释出境。
1906年2月,孙中山到新加坡组织同盟会分会,林文庆欣然入会,成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会员。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同时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
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1921年7月,任厦门大学校长直至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前后在厦大任职16年,为厦门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日治时期,林文庆被迫出任华侨协会会长,但战后仍受英国人、新加坡政府和各族人士的敬爱,《海峡时报》尊他为“新加坡圣人”。
1957年元旦逝世。
《南方晚报》的悼文写到他与厦门大学时,这么说:“先生为厦大牺牲的,不只十六年,而是最宝贵的后半世。假使先生当时不回国,继续在马来亚的领导工作,其成就何堪限量?‘淮南之橘,过江为枳’。要使受维多利亚世代的教育及思想,并在殖民地气氛中度半世的人物,去领导五四运动以后的学术界,其结果可想而知。试读先生在其英译《离骚》中的自序及吊屈原诗,其当时的心情,何异屈原!?”
陈嘉庚
原名陈甲庚,后改陈嘉庚,是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现厦门市集美区)。其父陈杞柏(Tan Kee Pek)系当时新加坡殷商。
1890年奉父命南来,在新加坡顺安米店习商,辅佐父业。1904年,开始独资创业。到1925年,资本已达叻币1200万元,人称东南亚“树胶大王”。

1909年,陈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园会见孙中山,次年与其弟陈敬贤一同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员会主席,捐献给孙中山及福建政府20万元。
1910年以后两度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1923年任怡和轩俱乐部总理,并创办 《南洋商报》。毕生关注祖国人民福祉,倾家兴学。从1921年厦门大学正式开学至1936年止,他独资维持了十六年之久,捐款逾400万元。
1936年陈嘉庚虽已经济破产,仍然关心祖国政局。抗战期间,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展开募捐活动,运送大批军需及日用品支援中国;另组织3200多名机工回华服务,参加抗战。
和平后返新加坡,1949年6月回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及10月1日开国大典。1950年5月回中国定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
晚晴园对海峡两岸的意义 孙中山在南洋革命活动的后继影响,至深且距。如果说,当年的新加坡华人社会,是分成“亲英”与“亲华”这两大社群的话,那么,孙中山在新加坡鼓吹革命的结果,是把“亲华”的社群,再分化为“革命派”与“保皇派”两个阵营。二十世纪初,代表保皇派的《总汇报》和代表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之间的论战,就是这一事实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孙中山的影响,鼓励读书阅报,宣传革命党的书报社,如同德书报社 (潮帮)、开明书报社(粤帮)及同文书报社(琼帮)等,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 从而提高了华人的政治意识,为1930年代所展开的新马华人援华抗日的救国运动,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可说是百年来中国一批有识之士,为寻求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系而展开的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的过程是既痛苦又曲折的。从维新运动失败开始,就注定了中国政体的改变,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进行。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系”的切入点。
海外华人对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在于思想与财富倒流,从而影响中国的政局。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只是推翻旧政权,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共c革命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则彻底完成社会阶层的重组。
从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经过了风风雨雨的建国历程后,中国终于在1978年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新道路。这是辛亥革命后继发酵的结果,也是这场革命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晚晴园的历史是新加坡华人历史重要的一环,当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研究,因某种需要而有所定调时,新加坡由于其特殊环境,再加上与孙中山的密切关系,这种超然的地位,可以将孙中山的研究、及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提升到另一个高度。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会面。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 也是两党领导人时隔66年的首次会谈, 在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有朝一日, 当两岸达致大一统的共识时,晚晴园可是最好再度相聚的地点, 因为孙中山毕竟是两岸领导人所能共同接受的一代伟人!
2016年12月08日完稿 本文原题《从新加坡视角看孙中山》 原载《孙中山和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转载内容略有微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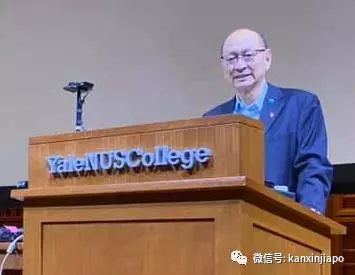
(柯木林,历史学者,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