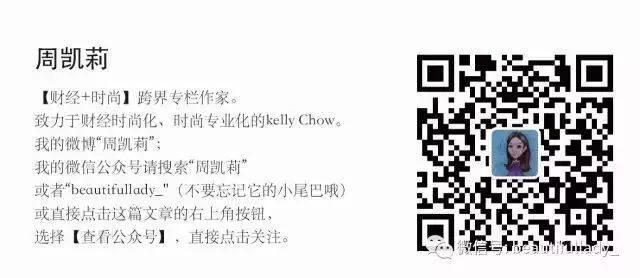我在一個雨後的暑日抱了筆記本一邊寫作,一邊等我的朋友,在新加坡金沙賭場大廳出口的咖啡座里。金沙酒店永遠是中國遊客的最愛,這裡有賭場、有各種大牌奢侈品店,還有無邊泳池和只要刷籌碼積分就能入住的房間。
我的身邊人來人往,有西裝革履的名流即視感的男人,也有蓬鬆著一頭茂盛的大卷髮,穿著無袖大花緊身連衣裙,大面積敞露小麥色肌膚的南洋女人。我沒有進到賭場裡,但我能想像出籌碼倒在絲絨桌面上的輕微聲音,和周遭不動聲色或七情上面的賭徒臉龐,還有扎著高馬尾、穿著黑色絲綢襯衫,畫著艷色口紅走來走去的賭場女公關。這是屬於他們的紙醉金迷的南洋。
我的南洋,則是這裡大多數中產階級生活的樣子。穿著優衣庫的運動服、踩著青草的露珠在對面屬於印尼的東部海邊公園慢跑,上班路上經過郁達夫和王映霞這一對怨偶分手的南天大酒店,放空的時候去利苑吃早茶或者去網紅西餐廳打卡brunch,在牛車水買中國商品時忽然聽到鄧麗君旖旎的歌聲,或者在周末臨時去附近的小島上做一下spa,在對著泳池的露天咖啡館裡發一會兒呆。
相比於大馬、越南、菲律賓等其他南洋國家,新加坡擁有極強的已開發國家風格,它是一個秩序、整潔、都市化的花園國家,以嚴格、有效的國家管理成為世界標杆。這一個小小的島國藉助於獨特的經濟發展方式異軍突起,但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完美保留了殖民主義時期的南洋風格,那一種懷舊的、溽熱的、帶著荷爾蒙分泌的性感。
來自中西方的不同文化在這裡衝撞,於是新加坡努力平衡著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中式與西式的文化。從傳統的中式價值觀而言,女性的被保護地位,通過一本《婦女憲章》(婚姻法)達到了某個高度,簡而言之,《婦女憲章》就是保護舊式女性在婚姻中的權利和地位,第一維度是為離婚創造各種法律意義上的「障礙」,第二維度則是設定離婚後的行事規則,比如前夫必須負擔前妻直至下一次婚姻前的贍養費。所以,在這一制度下,家庭主婦的地位是極受尊重的。她們負責專職養育小孩,僱傭月薪在3000-5000元人民幣不等的菲傭,在料理完家務之後,換上一條連衣裙、塗上艷粉色的口紅,出門喝喝咖啡、逛逛超市。
西式的文化價值觀則在另一個層面上浸淫著這一個國家,新加坡推崇男女平等的精英教育,絕不允許女童主動或被動失學。這兒的新一代女性大多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擁有獨立的思考能力,中產階級的孩子們喜歡攻讀專業類課程,優先選擇的職業是醫生、律師和金融分析師,專業人士的職業路徑頗受尊重。
我很喜歡我的醫生Dr. chua,她擁有我所欣賞的女人所有的樣子。她年近50,瘦的像一個香港女人,經典的bob頭,鑽石耳釘,和我一樣經常戴男式手錶,著艷色套裝。作為新加坡的著名婦產科醫生,她在繁忙工作之餘,竟然生育了5個孩子。她是第二代移民,從英國留學回來後,先在公立醫院熬了將近十年的資歷,便和朋友合夥開診所,冷靜果敢、氣場強大。這是我窮一生之力無法達到的境界。
以旅居者的視角仔細看去,這裡的大多數女人都帶上了堅韌、勇敢的別樣風情。如果說在高壓的都市生活里,香港女人們還有「揠生活」一說,那麼,在房價相對企穩、生活壓力相對較小的新加坡,女人們對於生活的尊重和熱愛,大多是自驅的,主動的。女人如何面對漫長的一生,一向是一個世界性難題,物化自我的年輕可愛固然能夠帶來某個階段加持的紅利,但在經歷愛與痛,享受生活之吻後,依然擁有自主選擇的能力,這是命運所能饋贈的慷慨禮物。
我在曾經的一篇專欄里描述過這樣的生活——在物質層面上,貫徹極簡主義者的一切原則:將繁瑣的對於食物、穿著以及其他的生活觀念,切實落實到味千拉麵、優衣庫以及紅眼航班這些務實的平價消費品之上。斷斷續續在新加坡住了幾年後,我感知到,這便是大多數新加坡國民對於生活的成熟觀點。任何的愛好和消費,都是發自內心的喜歡,而不是出於虛榮和為了證明自己。
不同於在烏節路或者來福士商場搶購大牌的遊人,本地人的「國民標配」是大褲衩和人字拖。大多數新加坡人,在時尚上放棄了自我,以追求舒適為主,但在追求個人愛好、充電培訓或者孩子的教育上都會投入不菲的金錢。我常常遇見在樂器中心自得其樂打鼓的白頭髮老年人,學費大約是一個月3000新幣。再比如一家早教中心,三個月每天三小時的幼兒培訓,大約需要5000新幣。
我曾做過一個社會實驗。幾個月前,我決定執行「斷舍離」的三清政策,從幾百條裙子裡,找了一批波西米亞風,設計精美,質量過硬,適合辦公室、或者旅遊度假、下午茶等各色場合的衣裙,以十分之一甚至更低的價格,在二手app掛牌。我的二手顧客里,有金融行業的華人分析師,也有帶著幾個孩子的馬來媽媽,還有在機場工作的斯里蘭卡移民。我和我的新加坡朋友阿花聊天,她對我說,和中國相比,新加坡的二手市場更為實效和發達,在本地的幾個二手app上,最好賣的依次是電器、嬰兒用品,還有運動裝備。
對於物質的淡漠,和對其極盡其價值的使用。這是已開發國家在國民經濟中發展中出現的「低需求」傾向。在威廉·曼徹斯特的史詩級巨著《光榮與夢想》中,對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大蕭條時代的「低需求」經濟進行過細緻入微的刻畫。已開發國家往往熟稔經濟發展的曲線定律,人們早已習慣了未雨綢繆。在當時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代背景下,中產階層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直線墜落,富豪們捂緊了錢包,卻也擋不住通貨膨脹下的貨幣貶值。稍稍幸運的是藍領們,因為不管經濟如何變化,人們總得滿足基本的吃穿住行,於是這些致力於服務業的人們本就過著消費水平不高的生活,相對受到的心靈上的衝擊還能勉強承受。
直到今天,美國人依然保留著大蕭條帶給他們的某些「低需求」習慣。大多數普通的美國家庭,在衣著上不太講究,一件舊T恤穿上幾年也並不在意;在吃上,更是漢堡加可樂,管飽就成;他們最快樂的事情,大約是一家人開著敞篷車享受公路旅行。這和發生在新加坡的生活方式有相似之處。
很多年過去了,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樣子。開車行駛在新加坡寸土寸金且清潔有序的市中心,經過現代都市風格的商場Mall,經過顏色雅致、排列整齊的住宅小區,也經過殖民主義風格的矮矮的黃黃的老式店鋪,擁有深淺不一的膚色的人們在新加坡河邊來來往往,前半生寫在他們的臉上,後半生便糾纏南洋的這一抹小小的島嶼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