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疫情之下新加坡面臨嚴峻的挑戰,新內閣保留了經驗豐富的資深成員,對4G領導團隊「扶上馬、送一程」,以應對並儘快度過當前的公共衛生和經濟危機。參照2004年非典結束後吳作棟辭去總理職務、由時任副總理李顯龍接任的先例,隨著疫情得到控制、社會生活回歸常態,王瑞傑及其4G領導團隊自會正式接棒。對於人民行動黨來說,從李光耀到吳作棟,再從李顯龍到4G團隊,領導團隊的過渡和世代交替早已形成了成熟的運作機制,但真正的挑戰已然不在黨內:隨著新加坡社會深刻變化,4G時代是否會見證一黨優勢制的正式終結?
自2011年「分水嶺」大選以來,以工人黨為代表的反對派發展壯大,在更多選區挑戰甚至戰勝執政黨,國會議席逐步增加,體現了新加坡民意的微妙變化。但這種變化不能簡單歸結為反對黨與執政黨實力對比的實質性轉變,而更多地反映了新加坡和國際社會大環境變化及執政黨對此應變欠佳。人民行動黨60多年長期執政積累的豐富經驗、塑造的專業經營團隊和設計主導的新加坡模式,的確使這個自然資源匱乏的東南亞小國創造了矚目成就,體現了可持續性發展。但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反權威反建制浪潮的推動下,執政黨與民眾溝通的軟實力尤顯欠缺。
不少選民認為,人民行動黨精英化、強勢、家長式的領導風格造成了一種高高在上的形象。但建國後一代的選民接受過良好教育,常年在繁榮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能更加成熟地獨立思考國家公共事務。說教式地告知選民「怎麼做」已經失靈,即便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危機之下也無法實現「聚旗效應」,因為更多的人開始思考「為什麼」。隨著反對黨陣營出現更多成熟、理性、專業且親民的候選人,選民有機會通過其它選擇發出聲音、向政治人物表明態度,尤其是提醒執政黨:人民的授權並非理所當然,執政黨應更加謙卑、具有能引起共鳴的共情力量。否則,僅憑傳統專業精英式的作風和民眾無感的數據,無法永遠維持一黨優勢。
2011年大選前夕,李光耀聲稱「如果阿裕尼(集選區)選民選擇工人黨,未來五年將活在後悔中」,遭到社會輿論激烈反彈,最終導致工人黨首次贏得該集選區並立足、連續勝選至今。全民敬仰的建國總理說教失敗,也促使人民行動黨反思並轉變傳統作風,試圖以更加謙卑的態度與民眾對話、傾聽民眾心聲。
新一屆國會任期開始之際,李顯龍於7月31日給執政黨新一屆議員發出公開信中,表示「我們必須期待國會有更尖銳的提問和辯論」【6】。同時,執政黨在堅持精英治國原則的同時,盡力吸納更多年輕力量進入政府,委以重任。
本屆大選人民行動黨提名多名40歲出頭甚至40歲以下的候選人,其中6名勝選議員進入內閣,最年輕(39歲)的閣員、新任貿工部兼文化、社區及青年部政務部長陳聖輝便是代表:擁有雪梨大學和哈佛大學學位、精通7門語言,曾在高盛集團、臉書(Facebook)、領英(LinkedIn)等大型跨國公司擔任高管;同時紮根社區做過15年義工,手把手教社區老年居民使用智慧型手機社交軟體,既具有精英的專業知識與素養,也親近平和、更接地氣。相比於年齡相仿、同為高管卻遭批「精英主義」的林紹權,陳聖輝們也許才是人民行動黨未來贏回民心的更優人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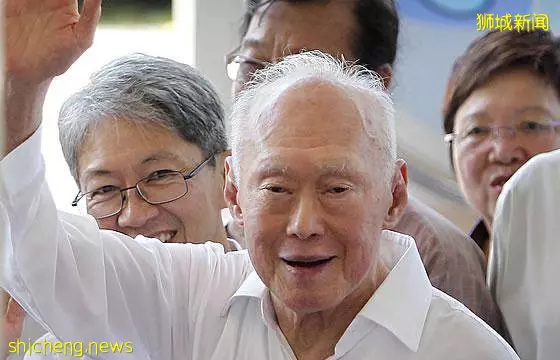
2011年大選期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選民後悔論」引發爭議,來源:Yahoo
除了誓言解決民生困難、實現經濟復甦,人民行動黨也坦承民眾對於政治多元化的訴求,主動採取措施變革政治體制,朝當前的一黨優勢制「開刀」。本屆大選後新加坡國會出現12位反對黨議員,人數創下建國55年來之最。隨著國會反對黨更加壯大,人民行動黨政府首次正式承認了國會反對黨領袖的職銜,並效仿英國議會正式列出這一職銜的職責條款和特權,包括在國會享有優先回應權,有權聽取政府在國家安全、對外關係、出現全國危機時的機密報告,在國會質詢、辯論和發言等方面享有與執政黨議員和內閣成員相同的權利。
正如李顯龍在7月27日新內閣宣誓就職儀式所說,政府將順應多元化這個不可抵擋的趨勢,讓政治體制發展和演化,以回應選民訴求。在宣誓就職講話中,李顯龍甚至呼籲反對黨不僅應該對政策提出疑問和批評,更應該能夠提出可行的替代政策,可見執政黨如今不只將反對黨定位為制約和監督者,更是將其視為共同建設國家的一份子。相比於父親李光耀動輒把「精英治國」掛在嘴邊,李顯龍很少提及這個概念。經歷了分水嶺大選,人民行動黨也逐漸接受新的現實:既然民意逐漸不支持國會一黨獨大,那就順水推舟、主動改變現有的一黨優勢制。
就政黨實力對比而言,工人黨等反對黨仍不足以挑戰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地位,只是起到」副駕駛「的監督制衡作用,同時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式的議會民主制下新加坡國會議事崇尚紳士風度,講究法治和程序規範,並不存在不少新興民主國家常見的政黨激烈惡鬥;人民行動黨對社會資源的實質掌控和「威權式法治」也有效遏制了反對力量發展壯大的可能性;新加坡選民對執政黨不完全滿意,但也無意選擇一個替代政府,而是希望有效敦促執政黨改善提高,而長期規劃、高效執行、保持清廉和及時糾錯恰是人民行動黨在李光耀多年領導下塑造的寶貴特質。
然而現階段一黨優勢製得以持續,不代表其未來能夠一成不變:反對黨的人才基礎和組織基礎不斷擴大,為替代政府逐漸積累條件;李光耀痕跡的逐漸淡化和新生代選民的比例增長,選民的心理和觀念也可以從量變形成質變,雖然可能需要幾代人的時間;如果人民行動黨的活力和紀律逐漸喪失,調節社會矛盾的能力不足,國內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一黨優勢制的難以為繼也不無可能。
隨著李光耀時代正式落幕,以及新加坡社會的發展進步,當代新加坡政治人物既不享有他的功績,也不具備他的威望和傳奇地位,更不可能像他一樣以「導師」的身份指教民眾選擇何種私人與公共生活方式。即使未來反對黨逆襲上台執政,也不可能重建李光耀時代的一黨優勢。畢竟21世紀的新加坡與獨立初期完全不同:1965年的新加坡,富足的家庭生活、劍橋大學法學院等精英教育經歷只屬於李光耀和執政團隊的極少數人;而2020年的新加坡「民智已開」、「國富民強」,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優質教育早已為不少中產家庭共享,大眾身處信息時代,對於公共生活的思考、認知和選擇判斷自然不再是少數精英政治人物的專利。
基於傳統「精英治國」和「技術官僚主義」的一黨優勢制在全球範圍內無不遭受民主化浪潮的衝擊,而新加坡也不例外。本屆大選後李顯龍政府一系列主動求變的行動,已然說明一黨優勢制至少要在形式上做出改變、與時俱進,方有延續的可能性。
而本屆大選傳遞的信號,正如新加坡最大的英文報紙《海峽時報》編輯沃倫·費爾南德斯的評論:「最終,多數選民似乎想要二者兼得——人民行動黨掌權,但國會仍有一個強大的反對黨予以制衡。」
參考資料:
【1】集選區(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簡稱GRC)是新加坡特有的選舉制度,也是一種選區,於1988年開始實行。根據這一制度安排,集選區需要3到6人組成團隊參選國會議員,勝選團隊所有人均當選為國會議員。實施集選區制度的官方依據是確保國會有少數種族的代表:角逐集選區議席的團隊至少其中一人必須是來自新加坡馬來族、印度族或其他少數族群。批評者則認為這一制度與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馳,且導致人少勢孤的反對黨處於競爭劣勢。2020年新加坡大選劃分了14個單選區和17個集選區,每個集選區設4到5個議席。
【2】Arian, A., & Barnes, S. H. (1974).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 A Neglected Model of Democratic Stability.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 36, No. 3, 592-614
【3】根據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和《國會選舉法令》,在國會選舉中,如果當選國會議員的反對派候選人少於下限,選舉官就可以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請若干名得票率超過15%,卻在大選中落敗的反對黨候選人加入國會,即非選區議員。非選區議員擁有的權力與民選國會議員相同,不過獲邀出任非選區議員的大選候選人可以拒絕受委。新一屆國會共104席,包括民選議員93席、非選區議員2席、官委議員(Nominated Member of Parliament)9席。
【4】「格里蠑螈」是一個來自美國的政治術語,指以不公平的選區邊界劃分方法操縱選舉,致使投票結果有利於某方。這個政治術語源自1812年美國麻薩諸塞州州長埃爾布里奇·格里(Elbridge Thomas Gerry)將某一選區劃分成不尋常的蠑螈(salamander)狀,以讓民主共和黨得勝。
【5】「副駕駛」策略是工人黨原秘書長劉程強於2011年大選期間提出的工人黨的「建設性反對黨」定位,即工人黨就像副駕駛的司機一樣,「不是去爭方向盤,而是去支援並時不時提醒司機,確保他夠清醒,能夠完成路程」。
【6】Lee Hsien Loong, Letter from PM Lee Hsien Loong to PAP MPs on Rules of Prudence on 31 Jul 2020,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Singapore. Retrieved August 1, 2020, from https://www.pmo.gov.sg/Newsroom/Letter-from-PM-Lee-Hsien-Loong-to-PAP-MPs-on-Rules-of-Prudence-on-1-Aug-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