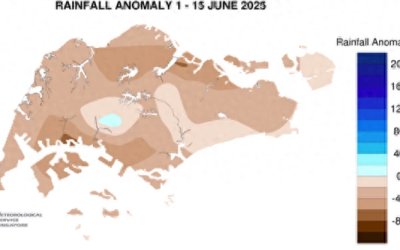中世紀歐洲的農業社會一般為軍事化社會,等級森嚴;都城築有防禦工事的城堡和巨大宗教建築,如大教堂。新的港口城市(或者叫「貿易港口」)依靠從印度洋進口奢侈品而聚集大量財富,其中包括來自印尼的香料。這些貿易港口由寡頭聯盟統治,他們更喜歡與競爭對手進行談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由於這些貿易港口所管轄的領土面積很小,他們的政府類型與王國不同。有些港口城市「與內地的聯繫少得驚人」(Fox,1971:62)。事實上,「有證據顯示,(商人)根本不覺得有必要歸屬任何政體」(Ibid.:69)。
各個族群在早期新加坡發展中起了什麼作用?汪大淵稱新加坡的首領為「酋長」。這個詞意味著他要向更高政治權威稱藩納貢。顯然,新加坡一直處於馬來人統治之下。這與14世紀末到15世紀初的巴鄰旁不同,那裡的首領為華人移民或華人移民後裔。汪大淵說龍牙門「男女兼中國人居之」,說明在他的想像中,中國人本「不」應該與當地人混居。畢竟在中國港口(中國很少有向外國人開放的港口),傳統的做法是將外國商人限定在番坊居住,而且不允許他們與當地居民往來。據歐洲人記載,在15世紀的馬六甲、16世紀的爪哇和17世紀的巴鄰旁,外國人被限定居住在特殊區域。
那麼,為什麼新加坡與大多數已知的古代港口不同,外國人在此可以與當地居民混居?這是關於古代新加坡的諸多疑團之一,也許永遠得不到答案。不過,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新加坡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有海外華人社區的地方,這一點是考古學和歷史學都證實了的。
1500年,馬六甲華人擁有自己的聚居區,也稱甘榜(村)。那麼,是官方限定他們居住在那裡的,還是他們自願聚居以求自保?在淡馬錫沒有「華人村」,這也許說明那裡很安全,華人也就認為沒有必要自己修建防護圍欄。他們似乎很樂意接受當地酋長的統治,因為他們中沒有甲必丹,也沒有實行其他治外管理制度。
周去非(12世紀)和趙汝適(13世紀)為前往東南亞的商人提供了詳盡的指南。1296年,周達觀第一次提及華人已經在東南亞長期居住。汪大淵又再次提到這一現象。15世紀初,數個華人聚居區已經在東南亞應運而生。
此後,東南亞與中國的聯繫被切斷。16世紀初的資料顯示,早期華人「住蕃」者已經融入當地。這種情況使得早期華人「離散社群」 (diaspora)的性質與重要性變得撲朔迷離。王庚武寫道:「如果我們不了解強大的、不可磨滅的華商一族,我們將無法展示華人移民的全部歷史。」(Wang1991:21)因此,研究14世紀新加坡,對多個學科領域,包括早期東南亞城市生活、早期東南亞貿易和中國移民史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意義。隨著研究進一步開展,無疑會出現新的研究問題。
新加坡到底是典型的,還是與眾不同、別具一格的馬六甲海峽貿易港口?鑒於我們目前的初級認識,要給出確切答案是危險的。不過,根據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們可以說,14世紀的新加坡具有一些非典型特徵,其中之一是土城牆。1973年,對整個蘇門答臘島進行了一次考察研究,有證據證明,只有一處前殖民地時期的居住區有土城牆包圍(Bronsonetal.,1973:57)。這個遺址為楠榜省的布貢拉哈約(Pugung Raharjo),但此地不是河畔碼頭。也沒有證據顯示這裡有過任何大規模生產活動。因此,它與14世紀的新加坡不同,更像是一處儀式中心,而非人口密集的城市。
新加坡的舶來品占很大比重,有些屬於珍稀物品,這說明有一部分居民的品味超凡脫俗,而且對許多舶來品非常熟悉。這些舶來品包括來自東南亞以外的、有特定文化內涵的枕頭和錢幣。這種特點也說明,新加坡在那個年代、那個地區都是獨樹一幟、與眾不同的。
對新加坡的進一步研究將澄清並改變前25年考古研究過程中提出的問題。不過,該研究的第一階段已經顯示,此項研究的學術意義非同小可。新加坡考古研究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古代重要貿易體制的諸多發展狀況,以及東南亞人和早期華人移民文化互動的性質。
很少有商業夥伴關係能夠持續2500年之久。新加坡地區(包括從巴鄰旁到馬六甲所在地區),與印度洋和南海的貿易歷史就跨越了這一時期。其間,王朝更迭,興衰沉浮,港口從一處沿岸遷往另一處,但地理因素註定讓這一地區存在一個交通運輸的重要結點。
海上絲綢之路六階段
海上絲綢之路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經歷了多個階段。在史前階段,已經連接起來的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為東南亞,經印度延伸至波斯灣。這一時期的證據包括印度珠子、碗器、手鐲和東山銅鼓。
由於第一階段沒有文字記載,所以我們通過第二階段了解海上絲綢之路最初的歷史。第二階段始於中國漢朝開始控制並逐漸漢化中國南方和越南北部之時,此時有中國史料可據。在中國人進入南海及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一個千禧年中,這條路上來往最頻繁的是馬來人和阿拉伯人。一些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在運送貨物過程中也帶去了自己的文化印記。少數敢於冒險的中國人逐漸進入這一地區,但他們總是刻意隱藏自己的行蹤,躲避因與外國人非法交往而招來的嚴厲懲罰,因此我們永遠不確定是否有過這樣一批人。
這一地區最早的貿易大港很可能是泰國半島上的三喬山,之後是越南南部的俄亥。統治俄亥的扶南王國對印度和中國各朝來說,都是重要的經濟和外交夥伴,直到它於公元600年前後滅亡。之後的末羅游、室利佛逝、婆魯斯和吉打王國紛紛脫穎而出,走上歷史舞台。中國史料和考古資料都顯示,到9世紀,馬六甲海峽南北兩端都建立起富庶的商業王國,出現了一個兩極格局,且長盛不衰,直到19世紀。
9世紀,一種新的貨物進入海上絲綢之路:中國瓷器。陸上絲綢之路運送的貨物局限於少量昂貴的奢侈品,如絲綢,而且用動物馱運才有利潤。海上絲綢之路則可以使用大型船舶運送大批量貨物。這些船舶由阿拉伯人和東南亞人建造、駕駛,就連中國人都嘆為觀止。唐代晚期,中國的瓷窯開始大量燒制高質量陶瓷用於外銷。我們無法估計這類商品進入海上絲綢之路對沿線各國經濟的影響,因為沒有留下這一時期貿易情況的文字記錄。不過,對考古學家來說,中國陶瓷的發掘,使此後這一地區的早期貿易以及其他方面的歷史面目變得清晰可見。
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三階段始於12世紀某個時間點。出海經商的中國人數不斷增加,標誌著這一階段的開始。這一階段開始的具體年代無法斷定,因為我們仍然缺乏這方面的文字記錄。出海貿易的商人本身也不願意拋頭露面,引人注目,畢竟中國朝廷禁止這種貿易活動。但隨著中國北方淪陷,1127年南宋建立,朝廷自身和社會大眾對海外貿易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中國人開始接受這種合法的、受人尊敬的行業。中國瓷器在東南亞的分布情況說明,由於中國市場對東南亞出口產品和對印度洋貨物的需求不斷增長,而且許多貨物經由東南亞轉運至中國,許多東南亞港口因此興旺發達起來。
在12世紀,中國人開始大批永久定居東南亞,但由於缺乏文字證據,這一點尚不能確定。直到14世紀,汪大淵提到中國人居住在新加坡,我們才有把握,認為存在海外華人社區(這些華人有別於在不同時期旅居海外的商人,也不同於單獨定居並融入當地社會的華人)。東南亞經濟與中國經濟緊密相連,中國錢幣甚至已經成為一些港口的交換媒介。這些港口包括13世紀的中國城,還有14世紀初的新加坡和滿者伯夷王國。1368年,隨著明朝建立,並實行打擊對外貿易與交流的海禁政策,海上絲綢之路的這一發展階段宣告結束。
明朝的建立標誌著第四階段的開始,從1368年到1567年,大約持續了200年。在這一階段,海外華人逐漸融入馬六甲、蘇門答臘和爪哇的當地社區。皇帝頒布的海禁法令,讓中國瓷器越來越稀缺,泰國和越南的陶瓷於是取而代之。同時,伊斯蘭教經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取代了佛教和印度教。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並未因為中國商人和商品的消失而衰退。琉球史料引用了馬六甲蘇丹芒速王1468年的書信,信里稱「幾代人都從未像我們今天這般富裕」(Reid,1993a:10),說明雖然東南亞港口商人渴望中國人參與海上貿易,但他們的參與並不是東南亞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第五階段,新加坡退出了歷史舞台,直到第六階段才戲劇性地再度現身。這一階段一直發展到今天。在亞洲海上貿易的舞台上,新加坡扮演了一個有趣的角色:略顯神秘,天賦異稟,有些階段光彩奪目,有些階段又黯然失色、無足輕重。今天的新加坡占據著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舞台。如果我們忽略新加坡從未離開舞台的事實,忽略它早在14世紀就展現出的發展潛力,那麼它的終場表現會令人驚奇。事實上,假如拜里米蘇拉沒有遭受14世紀90年代末那場突然襲擊而倉皇逃離,那麼新加坡的崛起之日就不會這樣姍姍來遲。
本文編選自《新加坡與海上絲綢之路:1300—1800》,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