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而言,在大國及大國關係主導、現實主義思維占據主流的國際關係中,大國對特定小國的認知和行為是後者國際定位的決定性標尺。以此來看,地理稟賦同樣是小國的「宿命」,它相當程度上界定了小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價值、角色及其行為選項。
第一,地理位置是小國國際地位和戰略價值的關鍵標尺。地緣政治學探究的是空間的政治意義,認為地理因素對政治行為和國家權力至關重要。英國地理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1861-1947)的「大陸心臟說」,美國海軍軍官、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關於海洋與國家力量關係的「海權論」,以及義大利的吉烏利奧·杜海特關於「制空權」的學說,分別從陸地、海洋和天空三個視角討論了地理因素對於戰略安全和國家權力的影響。其中,馬漢認為任何地方的戰略價值取決於「位置」或「態勢」、「軍事力量」和「資源」這三個基本條件,同時具備這三大條件的地方就會成為「戰略要地」,並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戰略要地意味著戰略價值和戰略關注。當代世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地理因素對地緣政治都具有重大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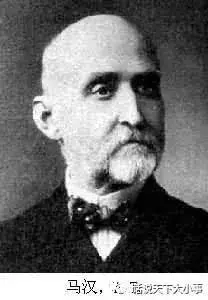
馬漢
美國海軍戰略思想家馬漢的海權論主張制海權對一國力量最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線能帶來大量商業利益,因此必須有強大的艦隊確保制海權,以及足夠的商船與港口來利用此一利益。馬漢也強調海洋軍事安全的價值,認為海洋可保護國家免於在本土交戰,制海權對戰爭的影響比陸軍更大。
地理位置賦予了小國特定的戰略價值。在大國視角中,位處全球戰略要衝的小國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戰略價值。這樣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構成了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和利用大國的重要政策籌碼。一些小國往往會「充分利用其經濟能力或戰略位置來影響大國」。地理位置優越的小國往往成為國際關係的「支點」,吸引著眾多大國的戰略關注;而那些遠離世界政經中心的偏遠小國則很難引起大國的戰略興趣,它們是被國際政治經濟遺忘的角落。
特定的地理位置意味著不同的戰略含義,並與全球戰略安全和國家權力相關聯。與世界權力中心、世界大國接近的小國,在海洋交通運輸中具有樞紐作用的地方,與戰略資源接近的國家都是大國關注的戰略要地。戰略位置與戰略資源一起成為吸引大國關注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戰略版圖中,中東、東南亞、中美洲、北非等地區具有顯著地位。譬如,東南亞位於太平洋、印度洋兩大海洋及亞歐大陸與大洋洲兩大洲之間,是世界海洋運輸最重要的交通樞紐,東亞國家必需的中東石油進口的必經之路。在聯合國秘書處列舉的8個重要國際海峽中,3個是處於中東的無替代航路的重要海峽,即曼德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荷姆茲海峽;另外5個全都位於東南亞,它們是馬六甲海峽、巽他海峽(爪哇和蘇門答臘之間)、新加坡海峽、聖貝納迪諾海峽(菲律賓東南部呂宋和薩馬島之間)、蘇里高海峽(菲律賓的萊特島和棉蘭老島之間)。這種「橋樑」式的戰略位置對於戰爭與和平都是至關重要的,它既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確保經濟運行的「生命線」。處於該地域的小國無疑具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更大的戰略行動空間。
職是之故,相較深鎖內陸及地理偏遠的小國來說,那些位處世界政經戰略樞紐的小國顯然是大國和強國積極關注、利用和爭取的對象。有吸引力的地理位置不僅能夠引來大國的經濟資源,而且有助於其對外戰略的制定和實施。
第二,地理位置塑造著小國特定的外部環境。與大國顯著不同的是,小國安全的主要威脅不會來自遙遠的國家,而是毗鄰國家和地區。在周邊國家發展繁榮、穩定有序,周邊環境安詳和平,區域安全治理機制健全的地區,小國安全將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歐盟小國享有的長久和平,與歐盟整體上的良好安全環境密不可分。相反,在一個發展滯後,遍布失敗國家的動盪地區,生存於其中的小國將不可避免承受更多的安全威脅。
地理位置也影響著小國與大國的關係。在任何體系中,地理和資源都是影響國家權力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是小國發展同大國關係的重要背景。譬如,與大國毗鄰通常帶來了脆弱性,但小國在面臨來自強鄰巨大壓力的同時,所具之戰略位置和戰略資源也在改善其地位。因此,相較其他因素,地理位置對小國外交的意義顯得更加突出。
一方面,一個國家在全球戰略版圖中的地理位置規定了其戰略價值,是吸引大國關注的重要因素,進而是它們發揮國際影響力的條件。1956年以前,英國一度將控制蘇伊士運河作為自身的責任和使命。美國關注巴拿馬海峽,德國則關心波羅的海出海口。
另一方面,處在地緣政治中心的小國往往成為大國對抗的焦點,因而處在危機四伏的外部環境中。在歷史上,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色列、丹麥、挪威、芬蘭等小國都無法避免地緣競爭帶來的巨大威脅。與此相對,愛爾蘭、瑞典、紐西蘭、加勒比國家、南太平洋島國則得益於遠離大國紛爭中心的邊緣位置,而免遭征服或者干涉的危險。對小國而言,地理位置是福是禍,最終還是取決於國際體系的性質。
第三,地理位置是小國對外戰略選擇的初始條件。在這個世界上,有的國家擁有許多鄰國,而有的國家則沒有鄰國。在不同的情況之下,一個國家與其鄰邦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具有不同的意義。與多個國家相鄰的小國,在外交上必然會傾向於考慮更多的安全威脅來源和多方位外交的發展態勢。只與一個國家接壤的小國,雙邊外交就是外交的優先考慮。比如丹麥(與德國)、甘比亞(與塞內加爾)、賴索托(與南非)、摩納哥(與法國)、卡達(與沙特)、聖馬利諾(與義大利),與強鄰之間的關係是這些小國外交政策不得不高度關注的因素。芬蘭和瑞典的安全戰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毗鄰大國蘇聯/俄羅斯的影響,不加入北約的戰略考慮之一是避免成為俄羅斯與西方潛在衝突的犧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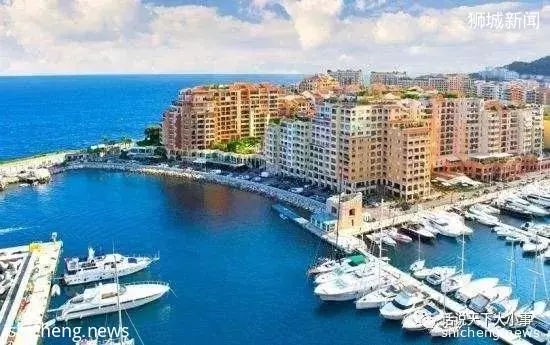
摩納哥
摩納哥是位於歐洲的一個城邦國家,也是世界第二小的國家(面積最小的是梵蒂岡),總面積為1.98平方公里。摩納哥地處法國南部,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線之外,全境北、西、東三面皆由法國包圍,為少有的「國中國」之一
地理位置深刻影響著小國的對外戰略選擇。小國不能塑造地緣環境,但地緣環境是影響小國對外戰略選擇的關鍵因素。遠離世界政治經濟中心的諸多島國,如南太平洋島國、加勒比島國和印度洋島國,雖然在經濟發展上面臨著不利的地緣環境,但在安全上也超然於大陸上國家間常有的紛爭,對安全戰略也就沒有處心積慮的必要了。然而,大陸小國,尤其毗鄰大國的小國往往會身不由己地介入到大國博弈之中,它們的外交戰略選擇就顯得格外重要了。對這些小國而言,在對外戰略選擇時,地區環境和大國關係是不得不思慮的重要背景。
仍以新加坡為例。獨特的地理位置既是新加坡對外戰略的重要砝碼,也是其「大國平衡戰略」構思和實施的前提。平衡戰略的要訣在於吸引諸多大國的戰略關注,而大國的戰略興趣往往來自戰略價值的多寡。新加坡的地緣戰略價值不言而喻,是關乎其生存的重要優勢。大國普遍認同新加坡的戰略重要性是它發揮這一優勢的前提。
李光耀指出:「芬蘭如果被鄰國蘇聯或瑞典侵略,列強可不必理會,因為這跟列強之間的勢力均衡沒有關係……可是如果沒有了新加坡,那就對它們非常麻煩了。我們必須好好照顧這一點;我們的地方雖小,可是幾乎全世界都公認這個小島具有極大的戰略重要性。」現實之中,新加坡奉行積極外交政策,廣泛結交諸多大國,「鼓勵世界上的主要強國知道它的存在」,並理解新加坡所具有的戰略意義,在大國交織的利益網絡和戰略關注中凸現自己的價值,從而嫻熟地操作大國之間的平衡策略。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對外戰略制定的依託。
第四,國土形狀對小國對外關係具有特殊影響。不同的領土形狀對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甚至對外關係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與此同時,地理位置與領土形狀的疊加效應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小國外交的基本取向。大多數國家的形狀或形態可以分為五種類型:一體型(compact)、碎塊型(fragmented)、狹長型(elongated)、孔眼型(perforated)以及凸出型(protruded)。不同領土形狀具有不同的安全意義。一體型國家具有環形形狀,是最容易管理的形態,有助於維持國家的統一,也比其他形狀的國家更易於防衛。碎塊型國家由許多海島構成,這樣的國家難以管理。狹長型國家對邊遠地區的管理非常困難。孔眼型國家的領土完全包圍於一個或多個國家,只有通過這個(些)國家才能到達被包圍的國家。如果兩個國家存在敵意,那麼被包圍國家就難以與外部聯繫。凸出型國家有狹長的土地延伸出來,突出地帶往往產生離心傾向。不言而喻,不同國土形狀的國家,其政經策略、安全思維、外部認知及對外政策各有差異,最終也影響了它們的外交取向和戰略手段。

智利
智利是世界上領土最狹長的國家,其國土南北長4332公里,東西寬90-40l公里,在地圖上看起來就好象南美洲的「裙邊」
以此觀之,地理因素對行為體的影響與意義從來都是不爭的事實。它對人類生活方式、社會政治文化和行為均具強大的建構性影響。在「小」的作用下,地理條件在小國政經發展中衍生出諸多突出效應。規模越小,這些效應就越顯著。可以斷言,絕大多數小國的政經發展與行為選擇相當程度上取決於其所擁有的特定地理稟賦。事實表明,小國的地理「宿命」既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對小國主觀能動性的無視。在現實性、競爭性國際體系下,地理效應是小國特性衍生的「副產品」。因為「小」,所以小國在生存發展中上得靠「天」,下得靠「地」。對小國來說,地理效應的表現方方面面,此理所必然,現實案例也俯拾皆是。相較大的國家,這難道不是小國的地理「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