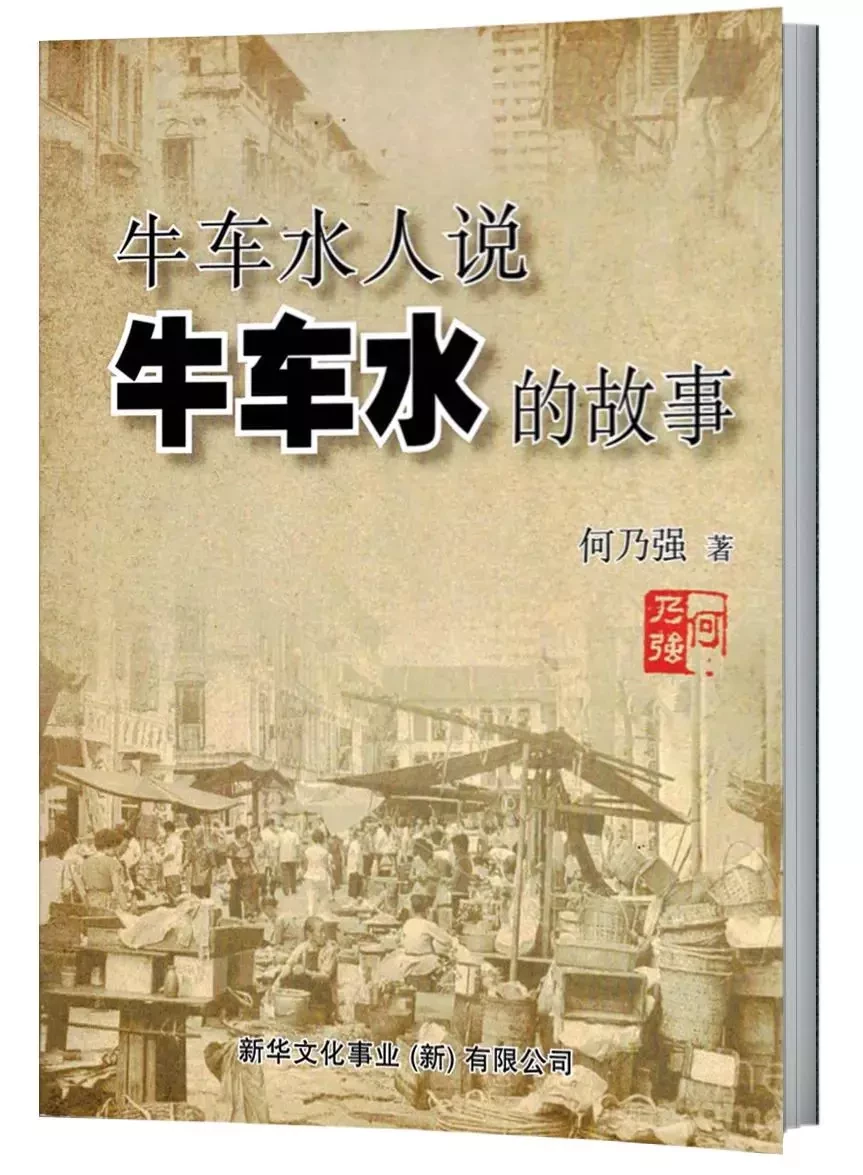
▲《牛車水人說牛車水的故事》封面
養正學友前輩何乃強醫生最近出版新書,稱為《牛車水人說牛車水的故事》。2023年12月10日的星期天,此書在合樂路富麗華河畔酒店發布。當天發言的除何醫生本人之外,尚有負責牛車水事務的部長楊莉明(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長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文友王振春和齊亞蓉。
何醫生說,他原本希望發布會能在興建於牛車水內的富麗華酒店舉行,但旺季之中該酒店的各個公用場所都已爆滿。幸好酒店老闆特別照顧,辟出新加坡河畔的富麗華一會堂舉行發布。在演說中,對牛車水的人和事,舊雨新知,何醫生都津津樂道,「感恩」之情溢於言表。
感激建國一代人的付出
有關牛車水,新加坡歷來出版過的文圖書籍也不少。何醫生自稱「牛車水人」,主要出於他自己所說的:「我的父母在1941年搬遷到牛車水居住,我在那裡長大和上學,度過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無憂無慮的生活。雖然成年後搬離牛車水,但因那裡有我的父業,我還時常定時回去辦理。屈指一算,我和牛車水的關係,至今已有80多年了……」
本書的第一個單元為「往事銘記」,何醫生在發布會上扼要回溯了當年的主要情景:1942年日軍侵略新加坡,戰機先大舉空襲南部人口密集的牛車水,有炸彈落在剛搬來幾個月的家附近。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英軍回到新加坡,這名牛車水小孩第一次看到金髮碧眼的「紅毛人」。就在當年的10月,小孩有幸進入學生剪光頭的養正學校就讀,打好了華文基礎。何醫生說他當時是養正的適齡生,班上個子最小,有些因戰爭耽誤了學業的超齡同學,畢業後不久就結婚了。
到了上中學的1956年,首席部長林有福的政府為了應付「中學聯」(新加坡中學學生聯合會)的學生暴動,出動警車,發射催淚彈驅散群眾,其中一個地點也在牛車水家門前的街道上。何醫生說,當時他躲在天台上觀看這一幕,百年一遇地嘗到催淚彈嗆猛的煙燻,畢生難忘。過後便是1963年的自治和1965年的新加坡獨立。最後,與他相守了58年的老伴(馮煥好),也出身自牛車水。
經過了這一切,作者感受到牛車水給了他「得來不易的幸福」。書寫牛車水的歷史,是為了感激建國一代人的種種付出,飲水思源。他認為,只有當我們記住過去,我們才有可能創造未來。
牛車水故事與新加坡
本書其他單元,包括「各行各業」、「書塾」、「醫院 醫生 醫師」、「人物」、「街道命名」等,可見所涵蓋的範疇是很多元的。令筆者最感興趣的是「街道命名」單元開宗明義第一篇文章《大坡牛車水、大馬路、小坡……》。文中引經據典,考究真正的牛車水區到底屬於哪個範圍。筆者2006年出版的拙著《曇花鏡影——牛車水的故事》,也曾探討過這個課題。

▲1919年的丁加奴街
其實今天為旅遊局所推崇,大力邀約外來遊客前來「打卡」的牛車水,確切來說是指大坡大馬路(橋南路)和大坡二馬路(新橋路)兩條大路,以及夾在兩路之間的多條橫街。與大馬路、二馬路形成工字形的垂直大街,就是海山街(今稱克羅士街上段)。著名的遊客街如丁加奴街等都聚攏在此,而位於史密斯街的熟食中心,今日已正名為牛車水大廈。傳統上,牛車水是萊佛士時代所劃分的廣府籍貫落戶區。

▲2023年的丁加奴街,多了商業味道,少了生活氣息
牛車水的正式英文/馬來文名稱是Kreta Ayer。然而,為了西方遊客識認上的方便,旅遊局把牛車水「英譯」為Chinatown。這一來,它的範圍就涵蓋了本地文史學者柯木林所認為的——北起新加坡河、南至麥士威路等等,「華人聚居甚多」之地,「名符其實的唐人街或中國城」。此「大牛車水」除了上述的廣府人區,也包括潮州人為多的馬真路、柴船頭,福建人為多的Telok Ayer港灣區。
連帶一提,萊佛士等殖民官以方言群劃分華人居住區的政策,「脫殖」後的某些新加坡人曾引為詬病,說是「分而治之」,目的是分化華人。但兩百年後回望,當時的政策或許也有無奈之處。據目前何著《牛車水的故事》,頁196指出新加坡歷史上最血腥的一次暴力事件,是1854年5月牽涉了潮閩族群的「五斤米大暴動」。暴動長達十天,死亡四五百人。書中指出,暴動的平定,警察總監湯瑪斯·鄧曼居功至偉。
維基百科中的Thomas Dunman(1814-1887)條並無收錄「五斤米」事件。但記這名英國人1840年以商辦助理的身份來到新加坡,三年後加入警界。鄧曼熱心社交與長老會活動,人緣甚好,1851年任Superintendent of Police(即香港所稱的警司),1856年升為Commissioner of Police(警察總監)。1871年從警察部隊退休後,鄧曼曾在今天稱為加東蒙巴登區的地帶種植椰園。以他命名的Dunman Road,即德明政府中學原來的創校地點。
何醫生大作發布會上,我注意到幾位發言人都各有取向。楊部長一心想知道,史密斯街和丁加奴街的命名從何而來。住小坡的海南人王振春先生,常到牛車水去是因一天能看三四部電影:這裡的大華、東方和金華戲院都相隔不遠。1997年移民新加坡的齊亞蓉女士,則認為牛車水和說牛車水故事的人都很「牛」。「牛」這個北方詞筆者不是很理解,或許是廣府人說的「威水」吧。
不過,無論你怎麼看今天的牛車水,何醫生所述故事,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對新加坡華人來說還是意義深長,值得繼續流傳下去的。
(作者為本地資深報人)
(本文首發於《源》167期,文章版權歸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源》雜誌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使用,歡迎朋友圈分享。欲閱讀更多《源》雜誌文章,請掃描以下二維碼,註冊成為《源》雜誌會員,即可閱讀更多精彩文章。為感謝讀者支持,即日起只要註冊帳號,便可享有一年的免費電子版雜誌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