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耀照片
2023年9月16日是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百歲冥誕。1959年6月5日,李光耀就任新加坡自治民選政府總理,時年35歲。1990年11月28日,吳作棟接任總理,李光耀繼續留在內閣,擔任內閣資政(Senior Minister)。李光耀擔任總理長達31年又5個月。
1959年李光耀就任總理時,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400美元,1990年卸任時,已增加到1萬2200多美元,1999年達到2萬2000美元。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評價《李光耀回憶錄》時說:「李光耀確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位巨人。在過去近50年里,李資政帶領新加坡渡過了一個又一個經濟和政治難關。他的遠見和理念不僅影響新加坡,也將影響整個亞洲的世世代代。」(本文直接或間接所引述的李光耀的話均出自《李光耀回憶錄》)
李光耀說:「對全世界來說,香港和新加坡是兩個相似的華人城市,規模大小也差不多。」他第一次踏足香港是1954年,稱讚面向海港的香港本島是個璀璨嫵媚的城市,景致迷人。他還稱讚「香港人勤奮,貨品價廉物美,服務一流」。
1962年,李光耀重遊香港。他說:「映入眼帘的儘是高樓大廈和百貨商店,足見香港在短短八年內已遠遠超越新加坡,走在前頭。」因此,1965年新加坡獨立建國後,李光耀幾乎每年都會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香港人如何克服困難,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他說:「我把香港當做獲得靈感和啟發的源泉」。
上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間,新加坡和香港經濟發展突飛猛進,跟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
新加坡和香港崛起的軌跡高度相似,在其他許多方面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中,新加坡和香港激烈競爭,互不相讓。2022年10月,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揭曉,新加坡一躍超越香港,位居紐約、倫敦之後,全球排名第三,亞洲第一,香港被新加坡「扒頭」。
新加坡和香港歷來就是你追我趕,相互競爭,天然就具有話題性。
1979年5月,我移居香港,1984年10月應聘到新加坡工作,至新千年開始時退休,在新加坡工作16年,回港後工作了6年,對港新兩地都有揮之不去的感情。因為從事語文工作,所以我特別關心新加坡的國家語言規劃。
說起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我認為李光耀是新加坡國家語言整體規劃的總設計師。為撰寫拙文,我重溫了《李光耀回憶錄》中的有關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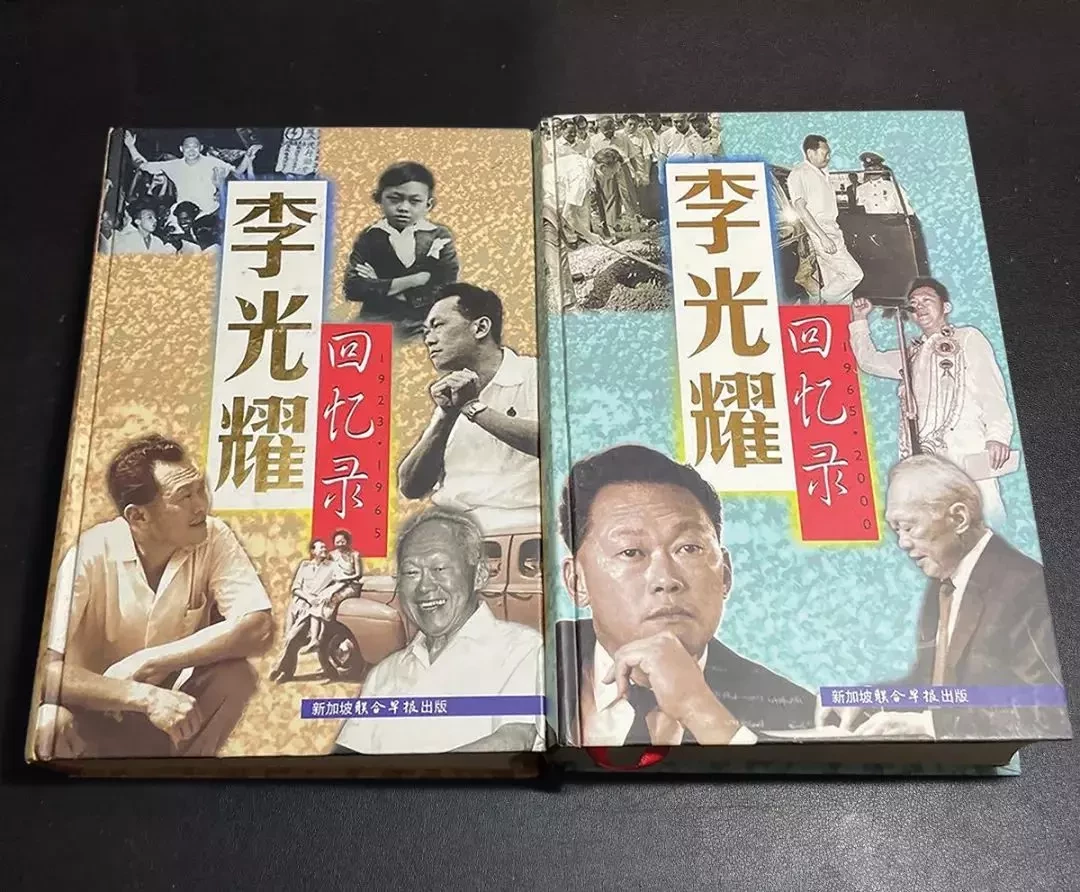
▲《李光耀回憶錄》
李光耀說:「新加坡從未有過一種共同語。在殖民統治時期,它是個多語種社會。」在1959年成立政府時,「我們的做法是維持現狀,讓四種官方語言——馬來語、華語、淡米爾語和英語共存」。當時,華人在家裡說的是新加坡本土不下七種華族方言里的一種,在學校里學的華語和英語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狀況怎麼可以長期維持下去呢?於是李光耀決定先為英文源流學校引進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三大母語教學。這一步受到所有家長歡迎,接著李光耀又為華文、馬來文和淡米爾文學校引進英文。然而即使這樣一先一後、平衡處理,還是受到華校生「死硬派」的反對。於是李光耀上電視明確表示,「我絕不允許任何人把華語的地位問題政治化」。
李光耀又何嘗不知道許多講華語或方言的家長對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結呢?因此李光耀耐心等待,他看到的是年復一年,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把孩子送進英校。李光耀深知,要每個新加坡人兼通英語和母語是吃力的事,但是如果只通曉母語,「新加坡就無法生存」,只有推行雙語政策才是前進的「最佳策略」。
雙語政策是新加坡的建國基石。事實證明,李光耀的決策是英明的、成功的。最近世人在媒體上所看到的關於TikTok總裁周受資的報道,不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嗎?周受資講的英語很標準,不帶「鄉音」,不是「新格利」(Singlish);周受資講的華語也很標準,不帶「鄉音」,不是新加坡華語,而是「很普通話」。因此有的中國網民質疑周受資體內的新加坡因子,這只能說明他們對新加坡國情還不是很了解。
大時代的歷史洪流塑造了李光耀的語言觀,同時引發了他的雙語教育政策的思維。新加坡的國情決定了新加坡的雙語政策,而推行雙語政策正是新加坡國情的重要內涵。金融投資家羅傑斯認為21世紀是中國和亞洲的世紀,於是選擇定居新加坡,讓兩個女兒接受華英雙語教育。他說:「新加坡成功地把焦點放在讓每個人都通曉至少兩種語言(也使用馬來語和淡米爾語),是它在過去45來一直是全球最成功的國家的一個原因。」
實施雙語教育政策,在華人社會就必須推廣華語,以減少乃至消除方言的干擾。為此,李光耀決定開展一場「講華語運動」(Speak Mandarin Campaign),從1979年9月7日開始至今,已經44年了。中國是從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開始「推普」的,迄今67年了。新加坡的「講華語運動」和中國的「推普」將永遠在路上。
接下來我就要講講跟新加坡「相似」的香港的故事了。
早在香港回歸那年,董建華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書就確定了具體目標:「由下學年起,我們會把普通話列入小一、中一和中四的課程;我們也會在二零零零年底前,把普通話列為香港中學會考科目。」1999年10月6日,他在第三份施政報告書中將基本法第9條之規定概括為「兩文三語」。他說:「特區政府的一貫宗旨,是培養兩文三語都能運用自如的人才。」「兩文」指的是書面語,即中文和英文;「三語」指的是口頭語,即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
「兩文三語」既是香港的語言政策,也是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培育香港人(特別是學生及就業人士)兩文(中文、英文)三語(粵語、普通話及英語)的能力」是香港中文教育的目標之一。「兩文三語」是對香港語言的總體規劃,令人不解的是,25年來,特區政府何以一直不在社會的層面推廣普通話呢?
新冠疫情後,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也向全世界敞開了大門,內地同胞和海外華人紛紛湧進香港,他們無論走到哪裡,聽到的依然是廣東話。今日之香港,社會用語、辦公用語、櫃檯用語、校園用語、教學用語、廣播用語、影視用語,甚至某些報刊用語,統統是廣東話。粵語依然一枝獨秀。25年來,特區政府不在社會上大力推廣普通話,難道有什麼難言之隱嗎?
最近看到一本新書,書名叫《細說香港民間推普七十年》。當「七十」這個數字映入眼帘時,我不禁一怔,原來上世紀50年代劉秋生先生來香港後,就推廣「國語」。也就是說,香港回歸前45年,民間的「推普」活動就開始了。
開卷閱讀,才知《細說》的作者張家城先生和他的同道許耀賜先生受業於劉秋生先生,許耀賜早在1971年就參與創辦「青年會(YMCA)大專國語研究學會」,同時結識張家城。1974年兩人義務為東華三院護理人員會開辦國語班,自編講義,採用漢語拼音,由此開始了在社會上通過開班授課等方式推廣普通話。1975年他倆創辦香港國語研習社,翌年改名為「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租用社址,開辦普通話學習班。張家城辭去白天的工作,成為研習社的第一名非受薪全職普通話教師,兼管社務,按授課教時計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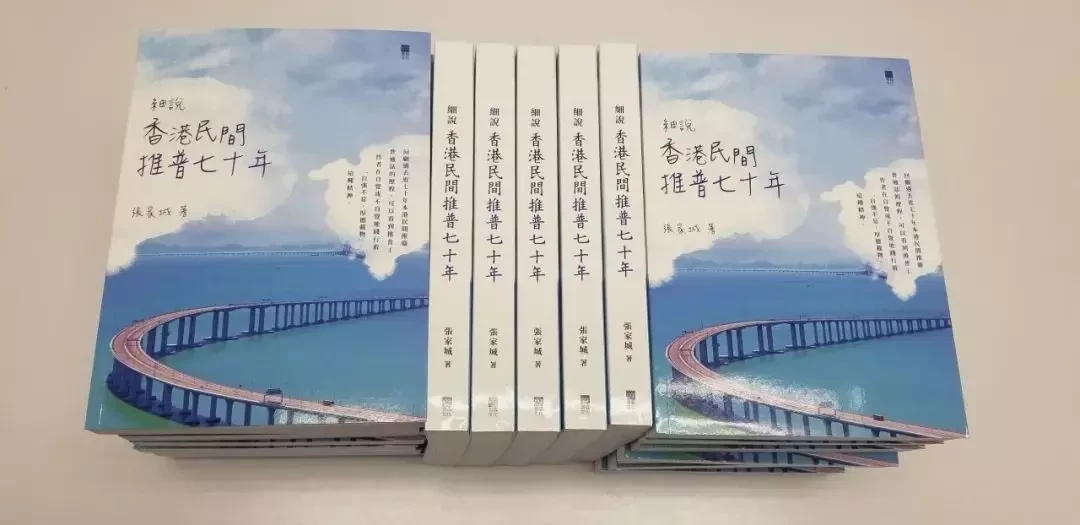
▲《細說香港民間推普七十年》
經過八年的努力,研習社終於發展成為香港民間最大的推普機構,有完整的教學體系(初級班、中級班、高級班、深造班、文憑班、貿易班、兒童班),有成套的教材《普通話課本》。1984年,張家城跟幾位同道創辦「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到2005年,「教育中心」開辦了一系列的普通話課程,出版了一系列的普通話教材,而在香港像「研習社」「教育中心」這樣的民間「推普」機構、團體或個人為數甚多。特區政府該不會視而不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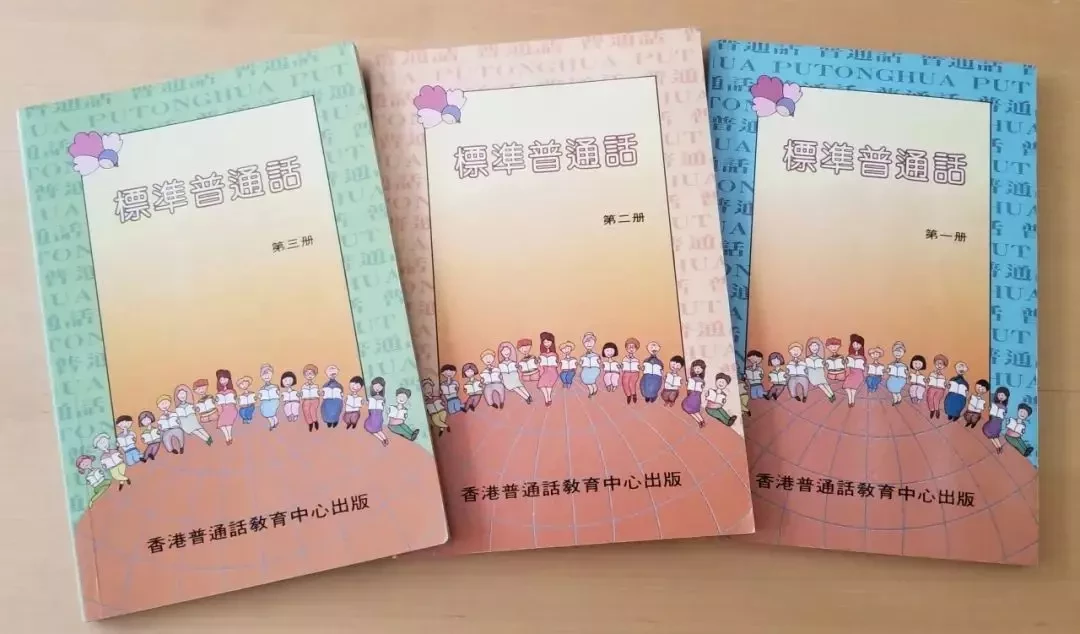
▲《標準普通話》教材(1—3冊)
許耀賜於1994年出任景嶺書院創校校長,2001年「研習社」創辦了科技創意小學,許耀賜是創辦人之一。這兩所學校,一小一中,除英語課用英語教授外,其他科目都用普通話授課。反觀絕大多數中小學,中文科採用普通話編寫的課本,教學語言卻是廣東話——用方言教華語課本,這種情形,全世界大概也只有香港才有吧?不失為特區特有的一道風景。

▲張家城(左)和許耀賜(右)
有人或許說,不是「一國兩制」嗎?我認為「兩制」是指社會的基本制度,難道一個國家的語言和文字(香港使用繁體字)也在「兩制」的範圍內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2條規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特區再「特」,也不能不依這兩部法行事吧?
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社會用語依然是方言一枝獨秀,香港特區政府在撥亂反正,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當兒,是否須要深刻反思反思,急起直追,在社會上「推普」呢?
今日之新加坡,華人華語,天經地義;香港呢,繼續擁抱著親愛的粵語。四年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說:「新加坡華人應該要儘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華語,讓孩子們掌握新語言。」新加坡的口號是:講普通話?是的,我能。香港能不能也這麼說:講普通話?是的,我能。
(作者為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報集團前語文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