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馬紹爾的訪華之旅
作者:林恩和(怡和世紀編委)
來源:《怡和世紀》第44期,轉自新國志網站,點擊閱讀原文瀏覽更多精彩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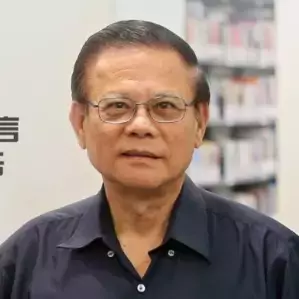
作者簡介
林恩和,《怡和世紀》編委。1951年生於新加坡,筆名河洛郎。曾任出版社編輯(1976-1978),出版並主編評論雜誌《拾穗》(1978-1979)。從事圖書零售批發及出版凡40年。文章常見《聯合早報》《怡和世紀》及其他雜誌。受邀擔任新加坡電視節目「新語研究所」第一系列和第二系列解題嘉賓。目前從事新加坡華語研究,為新加坡文物局的研究項目。出版的著作有《我城我語:新加坡地文志》、《我城故事:重訪新加坡歷史》。
新加坡自治邦首任首席部長馬紹爾一生多姿多彩,他在生命的不同時期,扮演不同的角色,各有各的精彩:他是新加坡歷史上最著名的刑事案律師,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政治人物,在最後的十五年又轉身一變成為一位出色的外交家。
和他作為傑出的律師和出色的外交官的角色比較起來,作為政治人物的他顯然比前兩者失色。1956年6月,他宣布辭掉首席部長的職務,面對黨內同志眾叛親離,成為政治孤鳥的他顯得鬱鬱寡歡。但是沒過多久,他就接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電報,邀請他到中國訪問。這個邀請讓馬紹爾心中的陰霾一掃而空,興奮不已。對他來說,這無疑是天上掉下了餡餅,讓他有機會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中央,聚焦在鎂光燈底下。
馬紹爾這次訪華對主客兩造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對中國來說,1955年4月中國總理周恩來出席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他在會議上提出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與會國家的共識;另一方面,他也趁出席會議之便,與印尼外長簽署了有關解決印尼華人雙重國籍的問題,並呼籲入籍華人應該積極融入當地社會和效忠居住國。中國可以借著馬紹爾來訪向正在尋求擺脫殖民地統治、爭取獨立的國家表達中國人民對他們反殖鬥爭的支持,同時也趁這個機會向東南亞其他國家闡明中國政府怎樣看待和處理當地華人華僑的問題,以減少這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對馬紹爾來說,中國不計較他失去首席部長的職位,給予他高規格的接待,讓他亮相政治舞台,有機會和一個重要的大國討論涉及新加坡政治議程的事並得到他們首肯,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剛好這時新加坡的貿易諮詢委員會也收到中國邀請,計劃組織工商業考察團到中日兩國訪問,委員會主席是馬紹爾的好友葉平玉。葉平玉於是向馬紹爾建議由他出任考察團顧問。由一位具有反殖政治光環的馬紹爾率團訪問中國,毫無疑問的將能增加考察團在中國政府眼中的分量和地位。
雖然說馬紹爾和新加坡工商考察團這次出訪中國,分別受到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和中華工商業聯合會的邀請,純粹是民間的交流。不過,在當年的冷戰氛圍下,出現不少雜音,也引起殖民地當局和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東姑阿都拉曼的疑慮。馬紹爾深刻認識到這次訪問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他是首位新加坡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受邀到新中國訪問,面對質疑和雜音,他力排眾議,一個由61人組成的各民族工商業考察團終於在8月中旬成行。
從8月14日到10月14日,馬紹爾此次到中國訪問歷時2個月,收穫頗豐。除了必要到訪的中國的政治中心北京,為了讓他多了解新中國的建設和民情,中國主人特地安排馬紹爾游遍中國的大江南北。首先是到中國東北,去了瀋陽、鞍山、長春等城市,參觀了東北的中國的重工業中心;接著安排他到西部的西安、蘭州和烏魯木齊參訪;最後到南部和長江流域一帶的城市昆明、重慶、武漢、南京、杭州和上海。馬紹爾訪華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期,這個時期可說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發展最好的時期。他參觀了中小學、託兒所、大學、法院、寺廟、清真寺(回教堂)、教堂、工廠、居民區,和中國社會有了近距離的接觸,中國人民團結奮發的精神,讓馬紹爾留下深刻印象。從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加坡初到被稱為竹幕後的新中國,一切是那麼的新奇,對馬紹爾可說是經歷了一場文化震盪,猶如愛麗絲夢遊了仙境。
馬紹爾在上海期間被安排與四位社會名流見了面,他們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南洋菸草公司的簡玉階、號稱「紡織大王」的永安紡織廠的郭棣活(David Kwok)和上海大中華火柴公司的劉念義(Julius Liu)。……這幾位名流都有海外留學背景,能與馬紹爾用英語直接交談。訪華期間他還兩次私下和林建才律師見面吃飯,林建才是馬來亞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之一,新加坡實施「緊急法令」時離開新加坡到中國。
不過還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馬紹爾在上海期間也探訪了猶太人社區。事緣上海猶太人委員會的主席阿伯拉罕(R D Abraham)知道他來華訪問,特地寫信給他,要他協助一些想到以色列的滯留在華的猶大人離境。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受到納粹迫害,許多人從歐洲及蘇聯來華避難,人數一度多達3萬多人。二戰後,猶太復國主義興起,這些猶太人紛紛響應號召回到以色列。紹爾訪華時,尚有5百多人因故滯留在華。馬紹爾趁與周恩來會面的時機,直接向他反映,使到這個問題迅速得到解決。
他在訪華期間還會見了許多中國領導人,包括副總理陳毅元帥、喬冠華、廖承志、彭真、羅榮基等。而最讓他耿耿於懷的一件事,就是在中國國慶宴會上沒有安排他與毛澤東主席和當時也到北京訪問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同桌。不過值得大書特書的也是他這次訪華的重頭戲是兩次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的會談,會談的重點自然是他早就準備好的問題,他想要知道中國政府怎樣看待新加坡華人爭取公民權,以及怎樣處理所謂「雙重國籍」的課題。雖然中國總理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已經清楚表達了中國政府的政策和看法,作為政治人物的馬紹爾希望藉由中國總理針對新加坡的具體情況,再次明確表達立場,不無為他個人撈取政治資本和博出位之嫌。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英國政府早已把華人公民權的課題列入新加坡憲制談判的一籃子計劃之中,中國政府的立場不會影響新加坡的憲制談判的進程。
不過,中國政府還是應馬紹爾要求,在10月13日的《人民日報》發表公報,正式說明中國對新加坡華人問題的立場和看法,其實這和中國與印尼於1955年在萬隆訂的關於雙重國籍問題條約的精神沒有兩樣,主要有四點:
1)中國政府樂見新加坡華人遵循自己的意願取得新加坡公民權,並效忠於他們的居住國。中國政府認為這有助於中國的利益和新加坡的和平與穩定,也有助於發展中國和新加坡的友好關係;
2)居住在新加坡的華人在自願取得新加坡公民權後,不再是中國公民,雖然他們仍舊保持和中國在血統和文化上的聯繫;
3)那些取得新加坡公民權的華人如果要入籍中國,必須根據新加坡法律放棄新加坡公民權;
4)居住在當地的中國公民必須遵守當地政府的法律,不許參與當地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們基本的權益必須得到尊重和不容歧視。
馬紹爾和周恩來的兩次會談可以說是在坦率和友好的氣氛之下交流,不過,兩人有時難免有交鋒,比如在反對殖民主義的問題上,兩人在認知上有明顯的落差,這也凸顯了兩人不同的鮮明性格,從附錄的「談話記錄」就可看出來。
我要感謝台灣政治大學的劉曉鵬教授提供給本刊「談話記錄」的稿本,這也是引起我寫作本文的動機。為了讓讀者更好了解「談話記錄」,筆者在必要的地方作了背景說明和注釋。為保持原汁原味,以及讓大家體會當年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語境,我們不對行文作改動,只針對錯別字糾正。
周總理第一次接見新加坡首席部長馬歇爾談話紀錄
時間:1956年8月19日
地點:中南海西華廳
陪見人:張奚若1、廖承志2、李哲人3、喬冠華4、吳茂蓀5
(本文未經總理審閱,如有錯誤,由紀錄整理人員負責)
馬歇爾6(以下簡稱馬):非常感謝總理接見。
總理:我們等了你很久了。
馬:感謝總理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表示歡迎我到中國訪問。我先前還不知道,因為我當時在日本,在那裡待了五個星期。
總理:在日本期間好嗎?
馬:很好。我非常抱歉,去年總理到新加坡7,當時我是新加坡首席部長,但總理到達時,英國當局沒有通知我,直到總理離開後,他們才告訴我。當時未能歡迎閣下,非常抱歉。
總理:當時我們去也是沒有計劃的,是偶然的。新加坡當局還是很好地接待了我們,我們也很感謝。
馬:我事前一點也不知道,直到後來在一次宴會上才知道,我當時非常氣憤。
總理:西方朋友與本地人的關係還是有些隔閡?
馬:距離很大。西方為了自己的目的讓我當首席部長,但是不讓我知道各方面的全部情況,只告訴我他們願意告訴的事,因此對於許多事不能知道真相。在殖民地的(當)這樣的首席部長,實在是一個令人難受的位置。
總理:要克服隔閡需要時間,要克服很多困難。
馬:……新加坡反殖民主義應該不帶種族成分,各種族應該彼此合作,否則就形成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現在新加坡人口中有76%是中國(華)人,15%是馬來人,8%是印度人,2%是其他種人。
總理:你的種族協作的思想很有意義,這在馬來亞也可適用吧?
馬:應該也可以。我在儘自己的力量做。馬來亞從英國統治下解放8(自治)後,他們著重主張政權應交馬來人。長期以來馬來人對在經濟上占優勢的中國(華)人有猜疑,這種經濟上的猜疑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更加劇了。馬來亞的中國(華)人做生意比較聰明,因而在經濟上占優勢,馬來人現在主張馬來亞應該是馬來人的馬來亞。因此現在馬來亞各種族不僅不和諧,而且彼此敵視。那裡的中國(華)人是願意合作的,但馬來人態度很強硬。
……(省略多段,參見閱讀原文)
馬:新加坡的情況是獨特的,絕大部分中國(華)人,如果他們選擇中國籍,這些人就都有可能變為中國人,新加坡永遠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人……。
總理:我先回答你一個問題:我剛才說,有些華僑選擇當地國籍後,又要求回到中國,我們不能拒絕他;但是在中國與印尼的雙重國籍條約中說得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還須先得到當地政府的許可。要所在國許可之後我們才能接收,所在國不許可,我們就不能接收。所以不可能一夜之間把人家統統都變成中國人。
這是回答你的問題,現在說第四點。
第四,新加坡的華僑是有其特殊情況的,在其他地方,所謂中國人是少數,在新加坡是絕大多數。
馬:在馬來亞華人占居民的40%,在比例上說恐怕僅次於新加坡吧。如果新、馬聯合,則馬來人占45%,中國(華)人在(占)44%,印度人占8%,中國(華)人與馬來人數字差不多,拉赫曼對這種情況很害怕。
總理:有形成恐懼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有殖民者造成的恐懼。
馬:直到今年以前,英國對馬來亞是控制得很緊的。但是說句公道話,馬、華之間的緊張是在英國統治撤退後才冒出來的。
總理:要知道印巴分治也是在英國人撤退時才發生的。(馬大夫)(指馬紹爾,可能是周總理口誤)。所謂華僑的情況,在新、馬與其他地方不同,在其他地方也各有所不同。因此條約不可能一樣。我們願意照顧各國的不同情況,以便使多數華僑能參加所在國國籍。以新加坡、馬來亞為例,絕大部分華僑國籍不能確定,這是個問題,應該設法解決。因此我們不拒絕,並很願意與每一國的政府或有代表性的當局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絕不想拖延,更不是想利用這個問題來進行擴張。
根據以上所說四點,我們必須達到諒解,所以現在說第五點。
第五,要使華僑選擇所在地國籍,不是很簡單的。須做極大努力,做許多說服工作,除了法律規定外,說服工作是必要的,我們也願意做這種說服工作。但是也要照顧華僑的保守性,他們過去習慣於雙重國籍。在印尼,反對《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的就是中國(華人)血統的人,你昨天說印尼不滿意,要知道這件事還沒有完,還在開始,還需要時間,還要做許多說服工作,當然,如果能把1,200萬華僑一天都變成所在國人,那就沒有問題了,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簡單的。我們人口很多,並不一定需要這1,200萬人,更不會用這1,200萬人進行擴張。我在萬隆時找華僑代表談話,當時萬隆和雅加達兩位市長都在場,一邊說,一邊就翻譯給他們聽。
我們希望華僑都選擇當地國籍,但不(不是衍字)是不能拒絕他們選擇中國籍,不能造成一種情況,好像新中國不要他們了,新中國不要他們,蔣介石要他們,不能造成這種情況。
……(略去一段)
總理:這也是一個因素,雖然這個因素在其他地方作用也許更大些。我們很願意你就新加坡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特點直接提出來交換意見,這樣可以找到更適合於新加坡情況的解決辦法。
馬:謝謝閣下。我現在不是首席部長,我以一個客人的身份談話。華僑問題得到解決就可以保持新加坡的穩定與和平。閣下所說的四項(原話如此)原則如能公開發表,將有更大的作用。在新加坡我是主張各民族平等和諧的,但有兩個困難:
(1)新加坡有23萬年紀較大的華僑(人)還沒有公民權,馬來人,混血人等都反對給他們公民權,我認為這些人的公民權應得到解決,但遭到各方面的反對、攻擊,包括一部分中國(華)人。
(2)在學校里我規定設立馬來文、英文、印度(淡米爾)文、中(華)文(北京話)四種語文課程,我把這四中(種)文字(語文)作為新加坡的正式文字(官方語文)。中國(華文)學校以中國(華語)教課,但在小學要學馬來文,在中學在(再)學英文,這在當地都是必要的,為此我們花了幾百萬元來辦學校,這為了使各民族平等和諧。但有些中國(華)人似乎已(以)反對政府為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