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眾矚目的2020年新加坡大選終於落下了帷幕,在很大程度之上,可以說每次大選的結果既是對過去五年之中各黨派,尤其是執政黨表現的檢閱,也同時反映了新加坡過去數十年中的政治歷史文化積澱在與現實情境對撞之後的情境展開,並將昭示著新加坡的未來格局。在此之中,人的因素自然占據了重要的地位,而其所揭示的新加坡國民性格的塑造,也同樣引人深思。畢竟,正視自己國家的本土文化並積極參與對自身文化的反思與建構將是決定新加坡國民未來的重要思想基石。
作為移民占據國民構成重要部分的國家,再加上袖珍國、多族群文化與語言的現實情境,新加坡國民就天然地帶原族群的文化烙印。無論是華族、巫族、印度裔還是歐亞裔,他們都將其族群的語言、宗教與傳統文化習慣帶到了這個彈丸之地。並且,此地除了是銜接全球貿易的中繼點之外,更是東西方、中印伊都多種文明碰撞交匯之所。
就某種意義而言,新加坡以其開放性而成為了一個縮小版的地球,無論是地理大發現、近代殖民統治,直至現當代的全球化與目前的逆全球化潮流,在這裡不僅會感同身受,新加坡更像是一個全球晴雨表,從中可以洞悉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一切。
以一個先天不足的國家而言,一直以來總是揮之不去的生存危機感就直接引發了本地從政治精英直到普羅大眾各階層的憂患意識。因此頗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建國一代,在政治體制方面採用西方傳統議會民主制的同時,卻在本國國民文化塑造上選擇了一條近於東方的路徑。時至今日,從我們對孩童德育課程的設計乃至日常行為準則的推尊上,都較為強調個人對於家庭、社會集體乃至國家的歸屬感,以及「秩序」與「法律」。
顯而易見,這使得新加坡國民不但養成了嚴格執法、講規則、有集體意識等諸多優點,尤其是遇到危機之時,會非常自然地遵守家長、族群領袖與政府的方針。這一點,比起美國在疫情仍劇的情況下,但即使是想要說服普通民眾戴上口罩都很困難,就更加反差明顯。
相比之下,我們就可以知道新加坡國民是一個會共赴時艱的多麼優秀的群體。這種情況自然也會招致負面批評,如做事過於死板而不會變通,為人容易瞻前顧後、缺乏主動性與創造力,且因對政府的依賴而顯得太過「聽話」等。但人類其實永遠是處在一個取捨與平衡之中,重點是何者對於新加坡人更為重要。
時至今日,新加坡精英治國的傳統理念依然可以有效地避免讓它受當今在各國泛濫的民粹主義影響,可使我們更有效率、更為正確地減少一些紛爭,比如黨派紛爭與族群割裂所導致的能量內耗。但這種精英治國的思想,在新加坡處在相對貧窮與發展的初級階段則更容易為民眾所理解,一旦經濟獲得長足進步之後,人們又會因為不但從小必須生活在層層競爭的環境之下,即使成年之後依然還會發現社會之中的階層鴻溝,以及衡量社會成功標誌物質標準的單一化,尤其總是強調國家危機的存在,也會削弱民眾的幸福指數。
比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普通新加坡人固然物質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一方面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金錢財富給我們帶來的邊際滿足感日益遞減,我們對幸福的標準水漲船高,並且我們也日益因失去了對貧窮生活的回憶而把今日的財富當成是理所應當。在此情況之下,對於精英治國、勤儉治國、排斥福利社會、強調競爭等一系列的治國理念都會在新世代之中受到強烈的挑戰。
李光耀先生生前就睿智地指出過,新加坡的未來一定會走向政治多元化,姑且不提這種多元化是否就會給新加坡帶來福音,但它是歷史的趨勢。這次大選之後,以工人黨為代表的反對黨崛起已然成為了一個無法忽視的存在。然而,這種以左翼民主為號召的政黨,在面對移民等問題時又會顯出某種右翼傾向。
說到底,新加坡的在野黨至少在目前看來還並未形成一套內部調和的整體治國理念與施政綱領。當然,這也與其所擁有的資源過於匱乏有關。但就民眾而言,除了以在野黨來制衡執政黨的投票動機之外,在對政府提出更多要求之餘,是否也應該反省自己的權與責的平衡?我們所要求的,終將與我們所願意擔負的有所關聯!
我們畢竟依然還處在打造新加坡國族的初始階段,那些我們共同經歷與正在經歷的歷史與現實、集體記憶與文化習慣,尤其是依然還處在變動狀態的新加坡整體價值觀,將會決定新加坡全體民眾的未來前景。而這些,並非只是我們投完票後就隨手可以交付給那些管理我們這個社會的少數精英,我們每個民眾的今後行為舉措,都像那一票一樣,同樣決定了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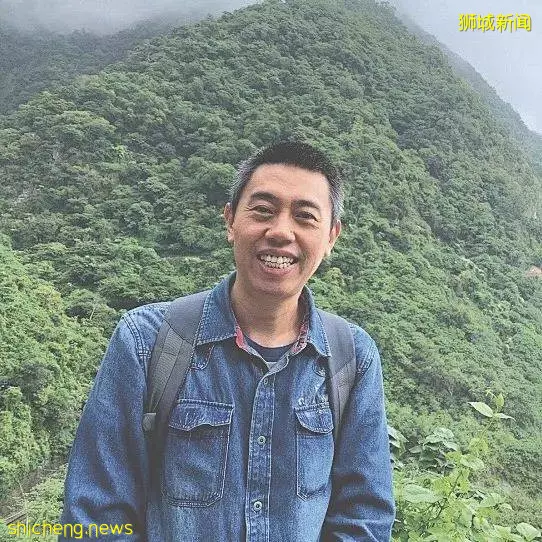
本地文史愛好者
紀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