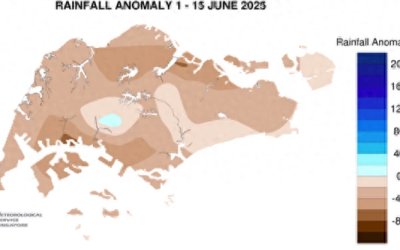《論領導力》是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與前國務卿基辛格先生於生前完成的最後一本著作。這本著作以6位他熟悉的傑出政治家為案例,詳細探討了領導力這一重要主題。其中,本文節選自關於李光耀的章節,講述了這位備受尊重的新加坡「國父」的領導才能。
基辛格 | 作者
《論領導力》| 來源
1 李光耀的遺產 1990年11月,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結束了他漫長的任期。為確保過渡穩定有序,他一點點地從國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來。他辭去總理一職後,先擔任高級部長,然後又擔任內閣資政,在隨後的兩位總理任期中依然保留著影響力,但逐漸淡出了公眾視線。
評價李光耀的遺產要先從新加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非凡增長說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長到1.19萬美元,2020年達到了6萬美元。GDP平均年增長率直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許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現代最了不起的經濟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紀60年代末,普遍認為前殖民地國家領導人應該保護本國經濟免於國際市場的壓力,並通過國家大力干預來發展本國自主工業。為了表現新獲得的解放,有些這樣的領導人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衝動的刺激下,甚至認為必須讓殖民時期在本國土地上落戶的外國人過不安生。這樣做的結果正如理察·尼克森所寫:
當今時代,評判領導人常常是看他們言辭的尖銳和政治的色彩,而不是他們政策的成功。特別是在發展中世界,太多的人白天聽了一耳朵話,夜裡睡覺卻空著肚子。
李光耀帶領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擁抱自由貿易和資本主義,堅持嚴格履行商業合同,吸引了眾多跨國公司紛至沓來。他珍視新加坡的民族多樣性,將其視為特殊的資產,不遺餘力地防止外部勢力干預國內爭端,因而幫助維護了國家獨立。冷戰時期,大部分其他國家領導人都採取了不結盟的姿態——在實踐中這經常意味著事實上默許蘇聯的意圖,李光耀卻把地緣政治的未來押在了美國及其盟友的可靠性上面。
在為他的新社會確定路線的時候,李光耀高度重視文化的中心作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和蘇聯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都認為,政治意識形態是決定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所有社會實現現代化走的都是同一條路。李光耀拒絕接受這個觀念,恰恰相反,他說:「西方相信世界必然追隨(它的)歷史發展。(但是)民主和個人權利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陌生的概念。」他無法相信自由主義主張放之四海而皆準,正如他難以想像美國人有一天會選擇追隨孔老夫子。
但是,李光耀同樣不相信這種文明差異無法逾越。不同文化應共存互容。今天,新加坡依然是威權國家,但威權主義本身並非李光耀的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家族專制同樣不是目的。吳作棟(和吳慶瑞沒有親戚關係)從1990年11月到2004年8月擔任總理。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的能力無人質疑,他繼吳作棟之後擔任總理,現在正逐漸從總理職責中抽身。他的繼任者將由下一次大選決定。新加坡在這兩位總理的先後領導下,沿著李光耀確定的道路繼續前行。
新加坡的選舉不民主,但並非沒有意義。在民主政體中,民眾通過選舉換人來表達不滿。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繼任者使用投票作為一種業績評比,讓當權者藉以了解自己行動的效力,因此讓他們有機會根據他們對公共利益的判斷來調整政策。
有沒有另外的辦法呢?另一種更加民主、更加多元的做法有可能成功嗎?李光耀認為不會。他相信,新加坡最初走向獨立之時,和許多其他前殖民地國家一樣,面臨著被派別勢力撕裂的危險。在他看來,存在嚴重族裔分歧的民主國家可能會淪入身份政治,而這又會加劇派別主義。民主制度的運作意味著多數人(對這個詞的定義五花八門)通過選舉建立政府,當政治意見發生轉變時再選舉另一個政府。但是,如果決定政治意見以及政治分歧的是身份定義這個不可變因素,而不是易於變化的政策差異,那麼民主制度正常運作的可能性便依照分歧的程度成反比下降。多數派會永遠占上風,少數派則企圖通過暴力擺脫自己被壓制的狀態。李光耀認為,由一群關係密切的同僚組成務實的機構,不受意識形態制約,重視技術與行政能力,不懈追求卓越——這樣的機構開展治理最為有效。他的試金石是公共服務意識:
政治對一個人有特別的要求,必須忠於人民和理想。你不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種召喚,和擔任神職不無相似之處。你必須感人民之所感,必須立志改變社會,改善人民生活。
明天會如何呢?就新加坡的未來而言,關鍵問題是持續的經濟和技術進步是否會導致向著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會過渡。這個國家的表現若是不如人意,因而導致選民尋求族裔身份的保護,那麼新加坡式的選舉就可能變質,成為一黨獨大的種族統治的證明。
對理想主義者來說,測試一個結構要看它能否達到固定的標準;對政治家來說,要看它適應歷史環境的能力。根據後者的標準,李光耀的遺產迄今為止是成功的。但是,政治家也必須經受他們所創立模式的演變結果的評判。對民意變化的容許程度早晚會成為可持續性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在大眾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義之間能否找到一個更好的平衡?這將是新加坡面對的終極挑戰。
如同新加坡剛剛誕生的20世紀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進入了一個意識形態的不確定時期。關於如何建立成功的社會難有定論。蘇聯解體後,自由市場民主自稱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卻同時面臨著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現和內部民眾信心的減退。其他的社會制度宣稱自己能更好地釋放經濟增長,培育社會和諧。在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在轉變中避開了這種鬥爭。李光耀對被他貶為「寵物理論」的僵硬教條避之不及。他一手設計了他所堅稱的新加坡例外主義。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論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勢需要隨機應變。他採取他認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發現並不有效,就馬上修改。李光耀總是在試驗各種辦法,學習其他國家的好主意,也從它們的錯誤中吸取教訓。然而,他從來不迷信別國。相反,新加坡必須不斷自問,它是否正在實現由它獨特的地理條件所決定,並由它特殊的人口組成所推動的目標。用李光耀自己的話說:「我從來不受任何理論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現實。我測試每一種理論或科學的決定性標準是,它管不管用?」可能柯玉芝教給了他亞歷山大·蒲柏的格言:「爭論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創造了一個民族,還確立了一個國家模式。根據本書導言中的分類,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構想出了一個民族,然後千方百計鼓勵他的國家在不斷變化的形勢中出色發揮,實現發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斷創造變成了習慣。此法能夠適用於不斷演進的人的尊嚴的概念嗎?
西班牙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說,人「沒有本質,他擁有的是……歷史」。在缺乏國家歷史的情況下,李光耀根據自己對未來的設想發明了新加坡的本質,在治理國家的同時書寫了新加坡的歷史。在此過程中,李光耀展示了他的信念的中肯,即政治家的終極考驗是他在「沿著沒有路標的路走向未知目的地」的途中如何運用判斷力。 2 李光耀其人 「環境造就了我。」李光耀去世前3年在一次採訪中如是說。他解釋道,在一個傳統華人家庭中成長的經歷塑造了他的個性,使他成為一個「自然的儒家信徒」:
基本理念是,一個社會要良好運轉,必須以廣大民眾的利益為重,社會利益先於個人利益。這是與(強調)個人首要權利的美國原則的主要區別。
李光耀認為,儒家理想是做君子,「孝敬父母,忠於妻子,教導孩子,善待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忠君報國」。
李光耀從不和人閒談。他相信,他來到世上是為了推動本國社會的進步,並為全世界的進步盡一己之力。李光耀絲毫不肯浪費時間。他來我在康乃狄克州的周末別墅做過4次客,每次都攜夫人前來,一般還會帶一個女兒。按照先前的約定,我會安排晚宴,邀請正在處理李光耀所關注的問題的領導人和思想家前來,還會邀請一些我倆共同的私人朋友。李光耀利用這樣的機會增進對美國事務的了解。我兩次在他的要求下帶他參加當地的政治活動,一次是參加一位眾議員候選人的籌款活動,另一次是出席市政廳會議。我按他的要求,僅僅對別人介紹說他是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
我去拜訪李光耀的時候,他會邀請鄰國領導人和他政府中的高官同我舉行一系列座談。他還會安排一次晚餐會,並和我單獨舉行討論,討論時間的長短取決於當時對我倆之中任何一人有所觸動的話題,不過從來都不短。所有的會見都在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莊嚴的總統府舉行。我多次訪問新加坡,李光耀沒有一次邀請我去他家,我也從未遇到過或聽說過有誰去過他家。這有點像戴高樂,除了阿登納,他也從不請人去科隆貝。
我和李光耀共同的朋友圈包括另一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和1974-1982年擔任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施密特。我們幾個人經常聚會(有時舒爾茨或施密特的日程安排不過來,就只有3個人聚)。第一次是1978年在伊朗,然後是1979年在新加坡,1980年在波恩,還有1982年舒爾茨被任命為國務卿後不久在帕洛阿爾托他家的陽台上。我們4人還參加了在舊金山北邊的紅樹林中的一次務虛會。碰巧和李光耀一樣不喜歡閒聊的施密特是舒爾茨的客人,李光耀是應我之邀。雖然我們幾人對具體政策的看法並不總是一致,但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承諾,如施密特對一位德國記者所說:「我們對彼此從來都絕對說真話。」能和李光耀交談說明獲得了他的信任,表示他在自己修道般專注的生活中給了對話者一席之地。
2008年5月,李光耀摯愛的妻子、陪伴他60年的柯玉芝突然中風,癱瘓在床,無法與人交流。這場苦難持續了兩年多。李光耀只要在新加坡,每天晚上都會坐在柯玉芝床邊為她大聲讀書,有會朗讀詩歌,包括柯玉芝喜愛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儘管沒有任何證據,但李光耀相信柯玉芝聽得到。李光耀對一個採訪者說:「她為了我醒著。」
2010年10月,柯玉芝溘然長逝。她去世後的那幾個月,李光耀破天荒地幾次主動給我打電話,交談中他說到自己的悲傷,特別是柯玉芝去世給他的生活造成的空虛。我問他有沒有和孩子們談過他的孤獨。「沒有,」他答道,「作為家長,我的責任是支持他們,而不是依靠他們。」柯玉芝去世後,李光耀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他仍然機智敏銳,但不復過去的努力奮進。他始終履行著他認為自己應該擔負的責任,直至生命盡頭,但他失去了靈感的來源,也失去了生活的樂趣。
我和李光耀做了近半個世紀的朋友,他在表達個人感情方面一直非常含蓄。最強烈的一次是2009年他主動送給我一張他自己和夫人的合照,上面寫著:「亨利,自從我們1968年11月在哈佛不期而遇,你的友誼和支持使我的生活從此不同。哈里。」李光耀對友情和對政治的態度一樣,重要的事情毋庸贅言,付諸言辭只會減弱其重要性。
李光耀辭去總理職務25年後,於2015年3月與世長辭。世界各地的要人云集新加坡,來向他致以最後的敬意。許多亞洲國家的政府首腦出席了他的葬禮,包括日本首相、印度總理、越南總理和印度尼西亞總理,還有韓國總統。代表中國出席的是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國的代表是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湯姆·多尼隆和我。我們都曾多次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與李光耀交流過。
葬禮最感人的方面是它展示了新加坡人民與他們的國父之間的親密聯繫。在李光耀的遺體接受瞻仰的3天裡,數十萬人冒著瓢潑大雨排隊等候到他的棺槨前致敬。電視新聞頻道用滾動字幕通知哀悼的民眾去致敬需要排隊等多久,排隊的時間從未少於3個小時。李光耀把各個種族、宗教、民族和文化聚合起來,造就了一個超越他自己生命的社會。
李光耀希望他的遺產能激勵而不是抑制進步。為此,他要求在他死後把他在歐思禮路的住宅拆除,以免其成為紀念場所。李光耀的目標是讓新加坡發展出能應對今後的挑戰、集中精力面向未來的領導人和機構制度,而不是崇拜自己的過去。他在一次採訪中說:「我能做到的只是確保我離開時,機構制度良好、堅實、廉潔、高效,政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麼。」
關於他自己的遺產,李光耀從來都採取冷靜分析的態度。他承認有遺憾,包括對他擔任國家領導人時採取的一些行動感到後悔。「我不是說我做的一切都對,」他對《紐約時報》說,「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了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一些惡事,比如不經審訊就關押人。」他引用一句中國成語說,「蓋棺論定」,意思是等到一個人的棺材蓋蓋上之後,才能對他做出判斷。
今天,李光耀的名字在西方已經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但是歷史比當代傳記更加悠長,李光耀的經驗之談依然值得迫切注意。當今世界秩序同時遇到了來自兩個方向的挑戰。一是宗教派別的激情壓倒了傳統的組織結構,致使整個地區陷入解體;二是合法性主張互相衝突的大國之間敵意日益加劇。前者可能會造成混亂的擴大,後者則可能導致災難性的流血。
李光耀的政治才幹在這兩種情況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一生的努力證明,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博取進步和可持續的秩序是可以做到的。他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為恰似指導課,教人如何在多種觀點和背景並存的情況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
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國經驗說明,決定一個社會命運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質財富,亦非其他衡量實力的普通標準,而是人民的素質和領導人的遠見。如李光耀所說:「如果你只看現實,就會變得乏味、庸俗,就會失敗。因此,你必須比現實站得更高,說『這也是有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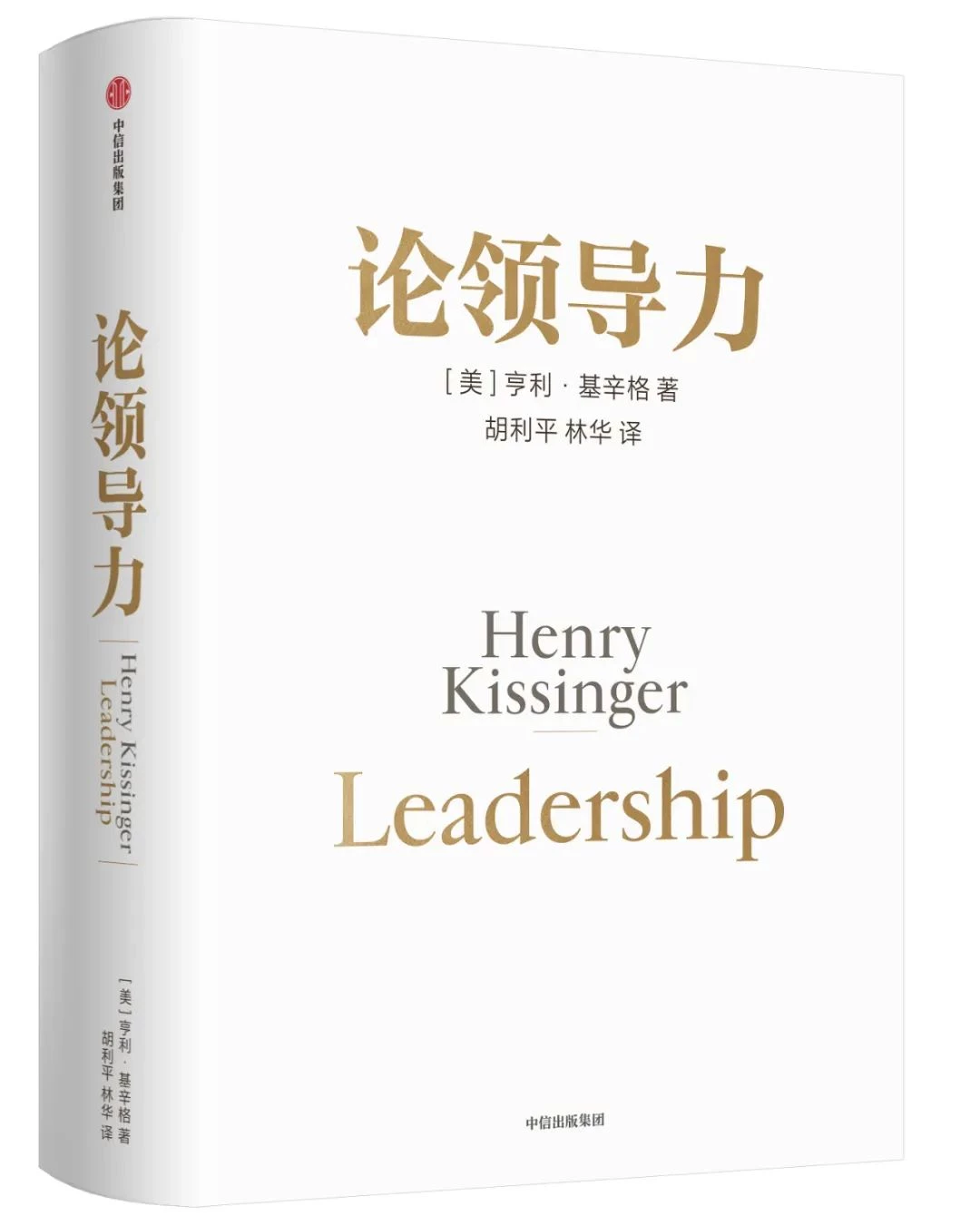
*本文整理自《論領導力》,基辛格 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