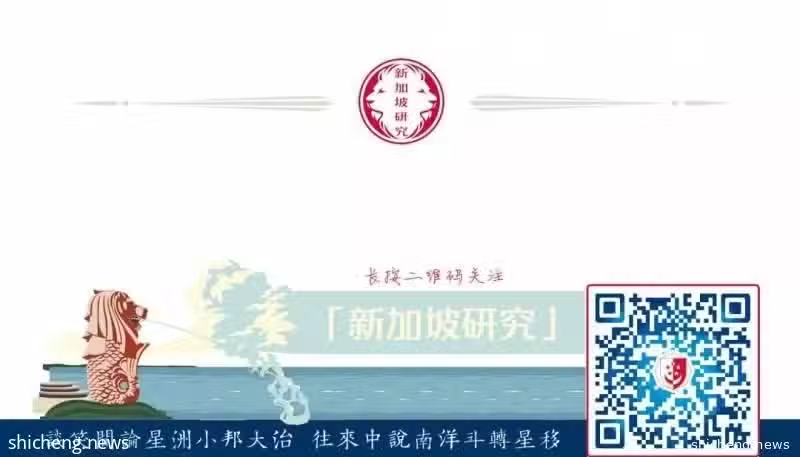三天後他在主持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典禮後告訴記者,在新加坡的發展過程中,政府的某些政策可能給某些人民造成不滿,但他勸告新加坡人要看大局。「無論如何,政策都是為新加坡的長遠利益而制定的。問問自己:新加坡今天的成就是怎麼取得的?政府做了多少正確的事才有今天的新加坡?」
李光耀是以務實的態度看待國家政策的演變。他主張,政策與時俱進:「電腦、網際網路、iPhone和iPad等新科技改變了世界,我們的政策也必須改變,以適應和接納新科技所帶來的生活方式。」但是他認為,新加坡良治的核心政策應該保留:「新一代新加坡人受過更好教育、有更豐富的國際視野,對治理國家的方式自然有不同的期望。因此,我們需要改變制定和實施政策的方法。但是,千萬別忘記我們的歷史經驗。那些促成新加坡成功的根本要素是千古不變的。比如:良治、廉政、任人唯賢和務實等。過去的經驗也協助新加坡人更好地了解新加坡立國所依賴的價值觀。」
行動黨及其政府很清楚新加坡的成功歷程和今後必須面對的「新常態」的政治生態。李顯龍總理分析說,越來越多元化的國人有不同的興趣與觀點,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民希望聽到不同的聲音,也希望拉近與政府的距離。他認為,新加坡政府既不能像瑞士和芬蘭等單一型國家般低調,依賴原有的制度執政;也不能如比利時或日本等國家走馬燈似的更換政府或首相。新加坡必須有意識地找出向前進的正確路徑,避免重蹈許多國家的覆轍。
2012年11月24日,李顯龍以秘書長身份在行動黨的一個研討會上呼籲,仔細思考黨在未來二三十年應扮演的角色,但也不忘提醒黨員在大選中勝出的重要性。執政黨必須代表政治的「中間立場」(Middle Ground),但它不該只單純消極地反映民眾的訴求,而應承擔引導並凝聚民意取向的責任。但黨的終極考驗更在於贏得大選,兌現競選時的政策諾言,對選民有所交代。
李顯龍說:「我們的責任是引導人民合理地看待個人的需求和新加坡的整體情況,這是我們的責任。……如果我們只是『好好先生』,一味附和別人的意見,我想我們將是失敗的領導人。因此行動黨的角色是領導新加坡和人民,說服他們支持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但最終我們必須在大選中獲勝,否則無法兌現政績。政府不可以毫無作為,而是適時根據最好的判斷採取最合適的行動。不過,我們也要審時度勢,作好重新檢討和校準方向的準備。決策時,我們必須做出適當的抉擇和取捨,執政就是這麼一回事。」
2012年12月3日,李顯龍總理在行動黨黨員大會上致辭時,再度強調治理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不能動搖。他告訴黨員們:行動黨作為執政黨,須要負起領導新加坡的責任。黨必須設定明確的方向,並且拿捏最佳的平衡標準,繼續帶領新加坡前進。「我們要很小心,不要在調整的過程中矯枉過正,一下子左,一下子右,搖擺不定,結果落得上下顛倒。我們也不應該捨棄那些一直對我們很重要的價值觀和原則。接下來黨必須帶領國人建構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並貫徹任人唯賢的制度,讓每個國民都有機會成功,從而打造一個既團結又包容的社會。」
其實,早在2008年,李顯龍總理在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就曾說過:「我們以前不完全是家長式的做法,現在也不完全是一味討好的做法,不是人云亦云。無論誰當領導,都必須有自己的看法和主意。如果你沒有主意,你不應該當領導。如果說只要大家同意我就做,這肯定會出問題。因為你當領導,除了聽取民意,你還有責任分析、了解、解釋問題,設法說服人民,爭取共識,使國家可以不斷往前走。」
政府一再重申,在放寬政治空間的同時,為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它將繼續以堅定立場治國,以免像其他一些國家那樣因政治對抗而陷入癱瘓,造成社會分裂,使投資者裹足不前,人民因而遭殃。
六 李光耀:國家發展的方向取決於年輕一代的決定
建國總理李光耀在2013年8月初面世的新書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個人對世界的看法》)里,針對新加坡政治的「新常態」表達看法。他說,新加坡政治像2011年5月大選這樣的成績,遲早會出現。人民行動黨取得60.1%的全國平均得票率,輸掉6個議席——這是自1965年獨立以來最糟糕的成績。行動黨在大選時幾乎囊括所有議席的情況,是不可能長期持續的……更重要的問題是,未來會怎麼樣?這得看行動黨如何應對新局勢,和選民做了怎麼樣的決定。
他說:「我無法預測未來的變數。但有一件事我很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終決定朝兩黨制方向前進,我們將註定平庸。如果我們對自己說,『沒關係,就讓新加坡成為一座普通的城市吧,何必嘗試做得比其他城市或國家好?』那麼我們將失去光芒,變成一個暗淡的小紅點。我們倘若走上這條路,我將為新加坡感到十分惋惜……兩黨制最大的問題是,最好的人才不會選擇從政。當選是充滿風險的事。選戰有可能招來對手的挖苦與羞辱,甚至惡毒的謾罵。要是你有才幹、事業有成,何必冒這麼大的風險參選,賭上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你多半會選擇避開戰場,過你的安逸生活」……
「新加坡百年後還會存在嗎?我不是很肯定。美國、中國、英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百年後還會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更早一代的新加坡人,建設這個國家時是從零做起,我們做得很好。當我領導這個國家時,我盡我所能鞏固新加坡的成就。吳作棟也是如此。現在,在李顯龍和他的團隊領導下,新加坡將來10~15年將會很好。但在那之後,國家發展的方向,就取決於年輕一代國人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不管他們最終做出哪些決定,我篤定新加坡一旦有個愚笨的政府,國家就會完蛋。這個國家將沉淪,化為烏有。問:行動黨會在這(出現兩黨制)之前失去執政黨地位嗎?答:我不肯定行動黨三、四或五屆大選會仍能繼續執政。」
七 新加坡人民高度信任政府
國際顧問公司埃德爾曼誠信指數(Edelman Trust Barometer)公布的數據顯示,在2011年10~11月之間接受調查的1000名新加坡人中,73%的人表示他們信任新加坡政府;國際的平均標準是43%。該機構主席兼亞太區總裁布萊恩(David Brain)分析:「新加坡人民對政府『做該做的事』的決心保持持續的高度信任,直接影響他們對政府表現的觀感。雖然有些新加坡人有時對政府的某些措施不滿意,但總體說,他們相信政府能夠在困難時期帶領人民克服危機。」
另一個國際機構克特昌(Ketchum)於2011年底透過網絡進行調查,了解受訪者對本國政治、商業和宗教界領袖的評價。3759名受訪者來自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印度、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新加坡等12個國家。調查報告指出:很多國家領導人的表現都未能達到人民的期望,尤其是歐美民眾對本國政治領導人更是大失所望。
從新加坡受訪者的反應看來,他們最重視的四大領導才能包括:領導人是否能冷靜應對危機(68%),以身作則(66%),以公開透明方式與民溝通(65%),以及是否能清楚勾畫出長期願景(63%)。報告說,新加坡人民對政治領導人的滿意度相當的高,認為他們在處理國際或國內事務時都展現有效領導素質。
埃德爾曼顧問公司於2013年5月發表各國人民對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s),包括政府的信任度調查,新加坡人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度排名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中國。事實上,新加坡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高達72%,居世界各國政府之首;人民信任作為公共機構的新加坡政府有能力做正確的事。
該調查也顯示,已開發國家的人民對他們自己的公共機構的信任度逐年下降。比如,歐洲國家的人民不相信他們的政府有能力解決財政問題。最顯著的是美國。2011年蓋洛普(Gallop)調查發現,低於10%的美國人信任國會,使它成為最不可信任的公共機構。
1990~2004年擔任第二任總理的吳作棟在哈佛大學談國內外挑戰時表示,新加坡內部越來越難達成共識。他認為:「新加坡的政治氣候已越來越開放和具競爭性。新加坡人現在受過更好教育、見識更廣,也善於使用網際網路。他們要為自己的未來爭取更大的話語權,也訴求他們的不同利益都獲得照顧。他們也更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特別是通過社交媒體。政府深具挑戰性的工作在於,須通過更大的政治多元性及國民參與度來凝聚共識,與此同時保留作出果斷反應的敏捷身段,進而迅速應對挑戰和機遇……這是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必須克服的新時代挑戰。」
八 結論
新加坡是實踐國會民主的國家,儘管它不全盤採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但連反對黨都不曾質疑新加坡定期的國會選舉是公正、公平和秘密的。中國學者張澤佳在《解讀新加坡的民主》里說:「新加坡具有西方民主國家所具有的民主框架,雖說是一黨獨大,但一黨獨大終究不同於我們國人所熟悉的一黨專政。一黨獨大,顧名思義,就是在一黨之外還有其他的反對黨,只不過這些反對黨因種種原因未成氣候,無法對人民行動黨造成實質性的威脅。反對黨是可以合法存在的政黨,它們可以宣布自己的政綱,不會因為在競選中或者在宣布競選之前被秘密關押拘禁。而人民行動黨,雖說在新加坡建國到現在未曾失去執政的地位,但黨的執政依舊需要通過定期舉行的一人一票的公開大選由選民選舉產生。」
署名「西瓜生魚片」者於2010年5月3日在「蓮池論壇」上發表的《新加坡的民主模式與美國有何不同?》頗有見地。他說:「人們一般把新加坡稱為權威主義體系,權力很集中。任何現代國家的權力都是集中的。權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說權力集中並不是一個價值判斷,並不能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好壞。民主國家的權力也是集中的。例如美國。美國是典型的民主國家,但其總統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很多學者稱其為帝王般的權力。
「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來保證這個好政府的。執政黨必須通過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選。因為有很多反對黨存在,儘管它們很小,但也構成良好的競爭壓力。反對黨本身對執政黨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制約,在國會裡只有少數幾個名額。但如果人民不滿意執政黨,在原則上大選時是可以支持反對黨的。因此,執政黨始終有壓力。執政黨的執政行為必須讓多數民眾滿意。」
他還說:「執政黨要代表人民的利益,這很重要。在這一點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發達的民主國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國精神是民本主義,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精神。在很多地方,人們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對資本和人民的作用爭論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處理了這些方面的平衡。根據我的觀察,新加坡的體制有一個好處,就是將『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人民行動黨要保證,先要選拔出幾個『好蘋果』,再讓老百姓投票來選舉。選拔是中國傳統的東西,而選舉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夠把兩者結合得很好。」
筆者很贊同上述兩人對新加坡政治與政府的觀點。新加坡政府治理之道都是以國家長遠利益和全民福祉為主要考慮。也因為如此,筆者相信,它將繼續獲得新加坡大多數選民的支持,為這個小島國創造更燦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