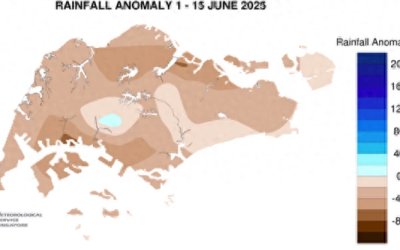宏茂橋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發展的市鎮,目前約15萬人居住在5萬多個組屋單位里。第259座圓形組屋是該區的地標性建築,高空看下來就像四葉草,從「火柴盒」式組屋外型脫穎而出。傳說中的四葉草代表希望、信心、愛情和幸運,整體就是幸福的象徵。
轉眼間40多年前的新鎮已經徐徐老矣,建屋局正著手興建新組屋來注入活力,不久後將出現新舊交錯的地貌。相信通過方言與馬來語的相關詞彙,更能追蹤宏茂橋百多年來的變化。

宏茂橋第259座圓形組屋是該區的地標性建築,造型像四葉草
紅毛橋?紅毛茄?紅毛驚?九條橋?
宏茂橋的英文名為Ang Mo Kio,1873年的地圖則出現Amokiah,也就是「紅毛驚」,中文老地名如紅毛橋、紅毛茄(番茄)、九條橋等同樣多姿多彩。這些地名都必須用福建話念出來才有神韻,譬如「橋」和「茄」同音,「橋」和「驚」則為諧音,可見此地的英文名轉譯自方言。
關於「紅毛驚」的由來,國家美術館所展示的版畫《Interrupted Road Surveying in Singapore》可看出端倪。話說新加坡開埠十多年後,建築師哥里門率領一群印度勞工,在湯申路一帶測量土地時,冷不防一頭猛虎從樹叢中竄出來,哥里門大驚失色,老虎也落荒而逃。在那個砍伐森林,人虎爭地盤的年代,「紅毛驚」可能是指哥里門遇虎這段情節。
至於「紅毛橋」,關係到哥里門之後的土地測量師湯申。他在湯申路與宏茂橋一道交界處興建一座橋,由於是「紅毛人」興建的,華人稱為紅毛橋。「紅毛茄」應該是紅毛橋的誤寫。「紅毛」是19世紀華人給予洋人的貶義性稱呼,殖民地官員竟欣然接受,紅毛橋就這樣用了一個世紀。二戰前,湯申路上段到羅弄泉的加冷河上,有九座大大小小的橋樑。原來承包商鋪設大水管,把貝雅士蓄水池的池水引進加冷河時,架起九座橋樑,民間索性把該地區稱為九條橋。

關於「紅毛驚」的由來,國家美術館所展示的版畫《Interrupted Road Surveying in Singapore》可看出端倪(攝於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甘蜜園、橡膠園到組屋區
1855年的《新加坡自由報》報道,分布在本島的75個甘蜜種植區中,共種植1200多萬棵甘蜜樹與160萬棵胡椒樹。宏茂橋的甘蜜與胡椒樹超過100萬棵,接近此水平的,只有格蘭芝河畔的巫許港和實里達河流域的汫水港。
雖然甘蜜園占據新加坡半壁江山,但含金量不高。當時新加坡的總出口額為1600萬元,甘蜜胡椒不及2%,但足以使一些商人(如甘蜜大王佘有進家族)富甲一方。
20世紀初,橡膠樹取代甘蜜成為經濟作物,宏茂橋跟著轉型,漫山遍野都是橡膠樹。
1970年政府援引徵用土地法令,鏟泥機轟隆隆地駛入民宅園丘。建屋局認為紅毛橋不雅,以宏茂橋這個新譯名來塑造全新的正面形象,亦不失保留該地區原名的色彩,可謂神來之筆。

宏茂橋1道的九條橋壁畫,葉耀宗繪製
從前的村落

宏茂橋的地貌變遷,根據1975年街道圖繪製
今天的宏茂橋細分為幾個區,包括宏茂橋、楊厝港、靜山、哥本巴魯、崇文、宏茂奎,這些都是從前的老地方。至於消失的地名有樹柅腳、水涵路、六巡村、無線電路,以及靠近甘榜羅弄萬國的十巡村等,可見20世紀的宏茂橋已經發展成為鼎盛的華人村莊。
哥本巴魯(Kebun Baru 新花園)是宏茂橋最早興建的組屋地段。甘榜哥本巴魯的原址靠近實龍崗花園,拆除時將地名遷移到宏茂橋4道,讓居民重續前緣。這裡的宏茂橋西市鎮公園的遛鳥俱樂部乃愛鳥人士的天堂,欣賞鳥兒清脆的歌聲之餘,亦結交志同道合之士。鄉村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曾自己動手,用樹膠圈和樹丫做彈弓射鳥,或許這就是「小鳥天堂」讓老居民流連忘返的原因。
現在的崇文區過去又稱「勵農村」與「禮弄芭」。「勵農」和「禮弄」都是馬來語lelong的音譯詞,原意是拍賣的意思。戰前那一帶的園主將膠園低價「禮弄」給他人,因此得名。

上世紀80年代初的宏茂橋鎮中心,圓形噴水池是當時新鎮的標誌(圖片來源:網際網路)
英軍留下來的宏茂奎軍營(Amoy Quee Camp)坐落在消失的紅毛鬼村約一公里外。宏茂奎原意為「紅毛鬼」,據說跟藐視牲畜生命的「紅毛兵」有關。上世紀50年代,實龍崗花園發展為英軍住宅,軍人前往軍營時抄近路,將車子駛入紅毛鬼村,撞死居民的家禽。村民怒氣難消,將這些紅毛兵稱為鬼,紅毛鬼村就這樣出名了。
從羅弄泉到湯申路上段的宏茂橋1道長約五公里,消失的樹柅腳原址靠近湯申路上段,「樹柅」就是福建話的橡膠。水涵路則在羅弄泉那頭。福建話的水涵指的是將麥里芝蓄水池的池水輸送到羅弄泉的大水管。
六巡村位於楊厝港路十條石的第14鄉道,是來自福建南安翔雲鎮的卓姓村民最集中的地方,這裡也住著同樣來自翔雲的梁姓和王姓,以及來自南安英都的洪姓人士,大家都是南安人。先民從中國農村帶過來的宗鄉聚居觀念隨著六巡村被拆除而消失了。
「六巡」名稱的由來富有傳奇性,其一是村裡有家規模龐大的「陸順」貨運公司,因此定名。另一說法是有位辦事認真的警察常在村子走動,村民愛戴這位「三劃」警察,把他左右袖章上的三劃加起來升級為「六巡」。
有村落的地方就有廟宇,今天宏茂橋的香火仍然旺盛,從前的鄉村廟宇組成宏茂橋聯合宮和六巡三合廟。也有些鄉間小廟走出去,譬如「青山內」的順興古廟、龍山廟和七寨廟,聯合附近甘榜山亭的七寨廟成立玄夫仙廟,在實龍崗北1道落戶。聯合宮可說是新加坡的特色,基於宗教土地的地契只有30年,鄉村古廟若要辦下去,只好集資來共存共榮。

宏茂橋西市鎮公園的遛鳥俱樂部
「青山」變「靜山」
宏茂橋發展前,現宏茂橋第3道和第5道之間有條約三公里長的青山路,從湯申路上段蜿蜒至實龍崗花園,乾旱的日子塵土飛揚,雨天則變成爛泥潭。青山路兩旁的山坡就是膠林和椰園。比鵪鶉蛋大些的橡膠樹種子耐磨耐熱,可以當子彈打鳥,也可以燙人取樂,這就是膠園孩子的童年了。
青山的村落偏僻深入,因此村民慣用「青山內」這個方言詞。青山內的居民主要是福建人和潮州人,村子裡挖井、修路和造橋三大社群功德都是村民親力親為。當泥濘路慘不忍睹時,村民便主動分工修築;木橋被山洪沖毀,村民自動購買材料,合力建造洋灰橋。橋基受到山洪侵蝕後,也是自己動手搶修的。
「青山」變成「靜山」有一段勵志的插曲。1945年,「公立青山學校」誕生了,不過好景不長,50年代初發展實龍崗花園,學校受到影響。陳六使的三哥陳文確捐獻青山內膠園的一塊地,親自監督學校的設計。為了激勵孩子們力爭上遊,他建議在青字旁加個爭。有了新校名「公立靜山學校」後,青山這個地區從此變為靜山。由於新校址在兩公里外,學生上學時在鄉間路上來回行走一個小時頗為平常。發展宏茂橋新鎮的時候,靜山學校留在原址,不過跟許多輔助學校一樣成為政府小學。

六巡三合廟是從前的宏茂橋鄉村廟宇組成的聯合廟
甘榜在新加坡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林高在靜山村長大,對於在地的景物人情都有細膩的記憶。譬如60年代裝置路燈後,村民再也不用摸黑走夜路了;沒有自來水的日子,水井幹涸了,年幼小妹、少壯婦女、纏足老嫗齊集在公共水喉提水;村子裡酬神演戲、男婚女嫁、治喪抬棺都是眾人的大事。這一切「不是契約,就是鄉村精神嘛」!如今青山內已經銷聲匿跡了,「那種簡單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故鄉」已經不存在了,可曾有「回鄉」的嚮往?林高更在意的,不是「故鄉」的實體,而是心靈的意義:「簡單里有可貴的價值,倘若把它的缺憾充實了,補足了,那簡單就是天長地久的幸福。」
林高眼中,多元是新加坡文化的特點,不過我們必須下苦功,將自己的文化與情感內化,才可能把多元的精髓發揚光大。新加坡的問題在於對文化的紮根,情感的守護都缺乏深刻的領悟,只是「意思意思」,因此難以彰顯傳統甘榜精神的現代性。鄉村被淘汰是無可避免的,問題是甘榜精神和人倫關係也被淘汰了。實際上,情感是文化的門檻,跨越門檻的當兒,必須知道什麼該扔掉,什麼必須保留,因為失去的不可能重來。

林高(站立者左一)的同學們到靜山村參觀,在他種植的甘蔗前留影,攝於1967年(圖片來源:林高)
新加坡人心中都有一所母校
除了靜山學校,宏茂橋還有友益、發明、啟明、中華、勵華、陶蒙、競新、培華、新正等鄉間學堂。現代宏茂橋曾經有一所歷史悠久,搬遷到該處落戶的大僑小學(取義「大埔華僑」)。經歷過兩輪整合後,大僑曾經吸收過崇文的學生,後來併入靜山小學,成為消失的華校。
大僑於1936年在小坡民多律(Minto Road)創校,三年後搬遷到林大頭巴剎一帶(後港五條石)。日戰結束後,學校於巴耶里峇蔥茅園復辦。80年代初由政府接管,位於宏茂橋第54街的校舍正式啟用。
楊欣怡是宏茂橋大僑小學的校友,離校多年後,對母校的一草一木依然歷歷在目:
「1997年,父母為我和雙胞胎弟弟在位於住家附近的大僑小學報名讀小一,舊校舍的建築與裝潢依舊留在我心中。小時候的我胃口特別好,每次休息時間,一定會點上我最愛吃的魚圓面和炒米粉。若有剩餘的零用錢,就會興致勃勃地跑去學校書店購買貼紙和有國旗標籤的橡皮擦來收集。2000年大僑和崇文小學合併,新校舍坐落在舊校舍旁,設施完善,環境寬敞又清新,校服從白衫青裙變成黃與藍的搭配。我和雙胞胎弟弟受到老師的寵愛,處處得到提拔,參與很多活動如演講和拼字比賽,豐富了我們的學校生活。我在大僑小學裡的時光是快樂且無憂無慮的。因為在小學打好了基礎,讓我在以後的學習路程里勇於追求向上,不論對工作或生活中不同領域都充滿信心。為此,我永遠感激大僑小學。」

大僑和崇文兩所小學合併時,兩校的同學們在新校園露營,攝於2001年(圖片來源:楊欣怡)
人的童年記憶里少不了故鄉,少不了母校,家園與啟蒙教育是孩子成長的港灣。不論路再彎,時光再遙遠,都難以磨滅烙印心坎的痕跡,維繫著人生的意義。這是我走訪宏茂橋,年長的林高和年輕的楊欣怡所給予我的心靈觸動。
參考文獻:
【1】宏茂橋地名趣談,《聯合晚報》1987年8月11日。
【2】林高,《記得》,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
【3】林高口述記憶,2020年6月10日。
【4】六巡三合廟龍獅團二十年特刊。
【5】莫美顏,《你住宏茂橋,可知名稱怎麼來?》,《聯合早報》1989年4月8日。
【6】歐倩慧,《ang mo kio是番茄?還是紅毛橋?》,《我報》2011年9月7日。
【7】《楊厝港區甘榜青山村民與政府合作搶修一崩壞橋基》,《南洋商報》1958年10月6日。
【8】楊欣怡口述記憶,202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