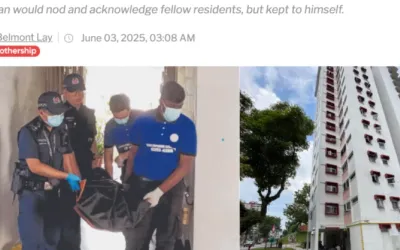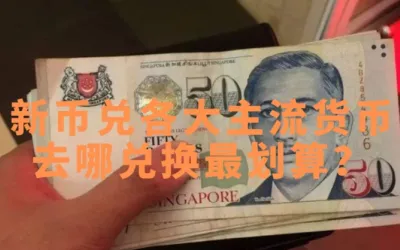面對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大流行,所有政府都實施了廣泛的政策來對抗外部衝擊。儘管目標相同,但各政府在應對危機的時機、政策重點和使用的政策工具上各不相同。已有的政治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影響政府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反應,造成差異。政府能力是一個政府組織官僚機構和分配社會資源的基本能力。最近,三位美國高校學者Wei-Ting Yen, Li-Yin Liu,Eunji Won和Testriono Nicola Belle合作,通過對亞洲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在新冠肺炎危機早期的案例對比分析,研究了政府能力如何影響政府應對COVID- 19政策的時間和配置。研究結果顯示,在病毒風險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能力較強的政府(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啟動危機應對更快,更廣泛地調動政府資源,並使用多種政策工具。相比之下,能力較低的政府(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在處理危機時反應更被動,將重點限制在與邊境有關的措施上,並在可以使用的工具類型上更受限制。該論文指出,在揭示政治制度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影響時,研究COVID-19應對過程而不是結果(即確診病例/死亡)的重要性。論文發表在公共管理類SSCI頂級期刊Governance上。
研究背景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大流行,所有政府都實施了廣泛的政策來對抗外部衝擊。儘管目標相同,但各政府在應對危機的時機、政策重點和使用的政策工具上各不相同。在世界衛生組織於2020年3月12日宣布COVID-19為大流行之前,亞洲各政府的反應差異尤為明顯。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3月期間,全世界對這種新出現的病毒的許多方面都不確定,比如它的起源、傳播路線和傳播速度。這種不確定性促使各國政府對這場危機做出獨特的反應。例如,韓國積極主動地調動其對檢測能力的關注。印度採取了更為被動的路線,只採用了少數與邊境有關的規定。那麼,是什麼制度因素解釋了早期亞洲各政府對COVID-19反應的差異?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有必要研究已有的政治制度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促成或限制政府的反應(Greer,2021)。在政府能力文獻的基礎上,本研究分析了政府能力——最低限度定義為政府機器實現政策目標的組織和官僚能力——如何影響亞洲各政府在2020年3月12日之前的COVID-19危機應對措施。該研究結合了政府能力文獻和政策設計文獻,並開發了一個框架,以了解政府能力如何影響響政府應對COVID-19的政策設計重點、拓展和全面性。
為了分析政府政策反應的差異,本研究對亞洲的五個國家和地區:新加坡、韓國、中國台灣、印度尼西亞和泰國進行了比較個案研究。通過官方聲明和文件,收集了從2019年12月31日(當時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COVID-19)到2020年3月12日(當時COVID-19被宣布為大流行並成為一個全球性問題)為應對COVID-19而採取的每一項政策措施。這五個政府發起的所有措施和法規都按政策項目和時間進行了排序。
政府能力、政策設計和COVID-19應對
政府能力是中央政府及其官僚機構滲透社會並分配社會資源以實現某些既定目標的能力(Besley&Persson,2009;Geddes,1994;Mann,1984)。因此,政府能力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最常見的三個維度是強制能力、行政能力和汲取能力(Hanson&Sigman,2021;Skocpol,1985;Soifer,2012)。強制能力是一個政府使用強制力迫使公民服從的能力。行政能力是一個政府設計和執行政策的官僚能力,而汲取能力是一個政府為其統治獲得社會資源的能力。這三個維度是獨特的概念透鏡,但相互關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包含一個自治的官僚機構,它具有設計和執行政策的合格能力,並擁有滲透社會(必要時使用強制力量)以獲取(和重新分配)資源的能力。政府能力是解釋政府成功解決公共衛生危機等抗解政策問題的關鍵組織因素(Christensen等,2016;Christensen&Lægreid,2020;Greer等,2020)。

政策設計先於政策實施,是「政府行使權力的手段」(Lindvall&Teorell,2016,第9頁)。沒有有效的政策設計,僅僅成功的政策實施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政策結果。儘管如此,適當的政策設計和政策工具對於實現政府預期的政策結果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有效的政策設計往往被認為是高政府能力的一部分。很少有研究揭示政府能力和政策設計之間的內在關係(參見Lindvall&Teorell,2016;Meckling&Nahm,2018;Mao,2021)。缺乏對政府能力和政策設計之間聯繫的關注是有問題的。無論一個政府的能力如何,它都需要合理的政策設計和政策工具來實現理想的政策目標。如果沒有恰當的政策設計,即使是最有能力的政府也可能在危機面前失敗。COVID-19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子,說明政府的高能力並不會自動導致低病例/低死亡率。
此外,政策設計在政府能力相關研究中往往被忽視,因為政策設計的研究往往留給公共行政或政策研究。為了充分解釋政府能力如何影響政府對COVID-19的回應,有必要將政策設計和選擇重新納入分析。
研究假設:政府能力作為政策設計的決定因素
為了解決像COVID-19這樣的抗解問題,有必要使用全面的政策工具並將它們捆綁在一起(Howlett,2005;Howlett等,2015;Peters等,2018)。政府能力影響政府在每個選擇的政策項目類型中利用綜合政策工具的程度。總的來說,高政府能力通過高水平的汲取和行政能力與危機管理中更多樣化的政策工具相關聯。在危機期間,更高的汲取能力意味著政府更有能力動員和與社會(即公民、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合作來汲取所需的資源,更高的行政能力意味著政府更有能力收集信息,做出相應的政策決策,並在社會中有效地實施政策(Mao,2021)。高度的汲取和行政能力,如果與政策工具聯繫起來,就會導致使用各種政策工具,特別是積極激勵工具、能力工具和通常具有象徵意義的工具(例如,呼籲政府團結),以產生更高水平的社會遵守和合作。
儘管政府能力的三個核心維度是相互關聯的(Hanson&Sigman,2021),更高的強制能力並不會導致使用更多樣化的政策工具。強制性權力意味著通過力量強制公民服從,這可以映射到權威工具的廣泛使用(有時與負激勵工具的組合)。由於維持秩序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能,當政府的汲取和行政能力受到更多限制時,其政府就更多地受到它們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類型的限制。無能力的政府更有可能在許多類型的政策項目中使用相同的政策工具,通常是授權工具,以實現預期的政策目標。因此,
H1:更高的政府能力致使政府通過更高水平的汲取和行政能力在政策項目中採用更多樣化的政策工具,而不是權威工具。
此外,由於政府能力還表明政府有能力在社會內部汲取和重新分配資源,預計這種能力將影響政府在應對COVID-19時能夠或希望側重於需要更多政府資源動員的政策項目類型的程度。一個汲取和行政能力強的政府可以協調機構間工作,並為COVID-19疾病防治工作調動更多的衛生資源。相比之下,在這兩個方面能力有限的政府也可能有開發衛生資源的意願,但實現其目標的能力有限(Chris-tensen&Lægreid,2020)。因此,
H2:在應對COVID-19時,汲取和行政能力高的政府需要調動資源的政策項目類型較多。
最後,當政府啟動危機應對措施時,政府能力也很重要。基於危機管理文獻(Comfort,2007),認識問題的嚴重性是政府採取行動應對不確定性危機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早期的認識,政府就不能正確地設計和實施應對即將到來的風險的行動。為了發現和評估危機,高度的行政能力是必要的,因為信息收集需要政府的信息能力和政府間/政府內部的合作。具有高度行政能力的,更有能力的政府可以在危機升級之前形成危機應對措施並採取預防措施,以便制定和執行有效的危機管理政策。相比之下,能力較弱的政府更多的是被動反應而不是積極主動。行政能力有限的政府更有可能在危機開始時袖手旁觀,直到風險水平已經很高,危機已經無法控制為止。因此,
H3:高能力的政府應對危機的主動性更強。低能力的政府在風險水平較高之前更被動。
總之,汲取和行政能力高的政府更有可能積極應對COVID-19時側重於需要調動政府資源的政策領域,並在選定的政策領域採用各種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能力低導致對危機作出被動反應,使用有限的政策工具,更多地依賴限制性的政策活動類型(如關閉學校、限制集會或封鎖),而不是能力建設性的政策活動。
個案選擇及資料收集
個案選擇
研究者們沒有進行全球範圍的定量分析,而是使用比較分析方法進行了深入的定性比較研究。本文重點研究了亞洲五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在2020年3月12日前如何應對COVID-19。首先,對早期階段的關注有助於防止同構和政策擴散的影響。由於靠近中國,東亞很早就知道COVID-19的威脅,政府也記錄了中國以外的第一例確診病例。大流行宣布後不久,各地開始模仿其他政府發起和採取的政策。在早期階段調查政府的反應,消除了大部分的政策擴散效應。此外,根據現有的應急管理研究,政府的風險認知(Comfort,2007)和早期反應決定了應急管理計劃的有效性(Comfort,2007;Kapucu,2008)。公共衛生的學者也強調了對流行病的早期發現和反應是遏制傳播的關鍵(Siedner等,2015)。早期階段設置的政策基礎對於應對以後潛在的暴發和不確定性也是至關重要的(Liu等,2021)。因此,探討各政府對COVID-19的早期應對措施,而不是研究它們在大流行被宣布後的應對措施,是很有價值的。
其次,根據地理鄰近程度和政府能力水平選擇案例。根據Hanson和Sigman(2020,2021)提出的政府能力衡量標準,選擇新加坡、韓國和中國台灣為高政府能力,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為低政府能力。這些政府都經歷過2003年的非典疫情。這種相似性可以減少任何歷史引起的混雜因素,這些因素會妨礙研究的內部有效性。此外,這些政府是不同的政權類型,新加坡和泰國是非民主政權。由於制度類型對政府如何應對COVID-19有獨立的影響,因此,在政府能力水平上混合不同的制度類型有助於找出政府能力對政策設計的真正影響。
數據收集
研究者們收集了五個政府採取的所有與COVID-19有關的行動。每個作者都熟悉其所負責的政府的語言和語境。這些政府回應來自各種在線來源,包括政府網站、當地政府在線網站和當地政府研究機構的報告,並按時間順序排列。他們將數據與牛津COVID-19跟蹤器(OxCGRT)進行了比較,以確保準確性和可靠性。這種比較能夠發現,當地報紙報道的一些政府措施不在OxCGRT列表中。具體來說,OxCGRT的數據並沒有記錄政府在2020年1月1日之前對COVID-19的反應。作者收集的數據包括2019年12月31日中國正式通知世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存在之前各政府的行動。因為這項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對COVID-19的早期反應上,這些早期反應尤其重要。此外,OxCGRT提供政府的回應(例如旅遊警告),但沒有包括詳細的政策內容(例如旅遊警告是否施加旅遊限制),這對編碼過程不利。因此,為了確保政府反應的全面性和編碼的準確性,不直接使用OxCGRT,而是使用OxCGRT作為比較,以三角測量自己的數據。
對於每個案例,對政府反應進行了如下編碼:首先,修訂了Cheng等人(2020)使用的16種政策項目類型,並使用該框架對政府關注的政策項目類型進行了分類。其次,使用Schneider和Ingram(1990)的政策工具類型,根據其基本機制和工具對每個政府反應進行編碼。將政府發起的行動或跨不同機構/部門/部門的合作編碼為能力工具,目的是「使個人、團體或機構能夠做出決定或開展活動」(Schneider&Ingram,1990,第517頁)。最後,編碼了旨在了解更多關於COVID-19的性質或發現解決方案的政府行為作為學習工具。例如,檢測開發和COVID-19的研究/調查是學習工具,因為這些行動是為了了解大流行病初期階段的情況和性質而開始的。為了確保編碼之間的可靠性,每個作者都進行獨立編碼,並通過遵循上述編碼機制完成編碼。在獨立的編碼過程之後,比較和評估了編碼。
政府能力範圍與COVID-19應對措施
比較案例分析可以產生有用的分析結果,因為這些案例在能力範圍上占據不同的位置,使能夠梳理出政府能力如何影響一個政府對COVID-19危機的反應。下面的分析得出了兩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