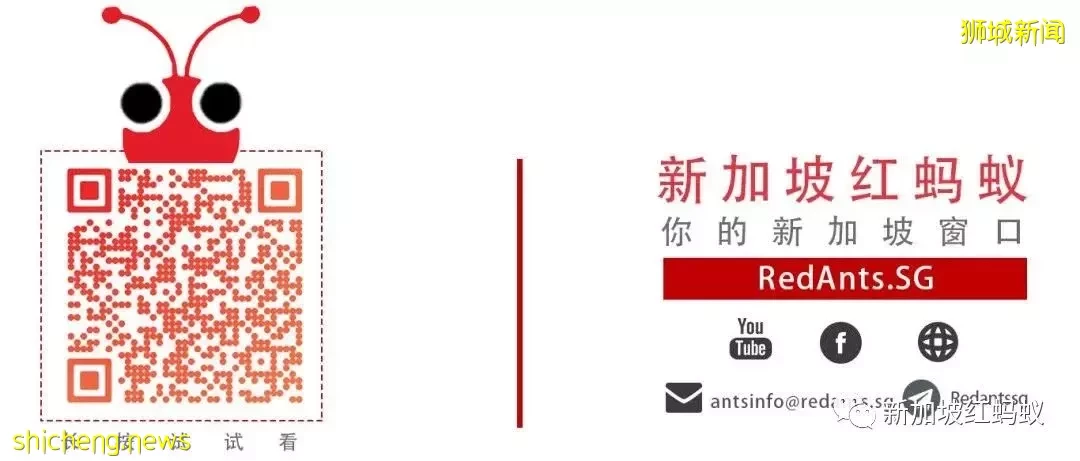義工包裝著裝有各種食品和家庭用品的「福袋」,準備送給有需要的家庭。(公益金提供)
作者 祥子
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Centre for Asian 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CAPS)在7月12日發布了一項名為「2022年行善指數」 (Doing Good Index 2022),針對17個亞洲經濟體內的2239家社會服務組織展開調查研究。
結果顯示,新加坡與台灣並列為「最有利行善的亞洲國家與地區」。
乍看之下,這句話不容易理解,還以為是指新加坡人和台灣人一樣都是最好善樂施的人,事實上說的是政府行為。
新加坡具有良好的監管框架,為非營利組織、社會企業和慈善機構提供重要的支持,並且在慈善捐款的政策上給予250%的稅收減。

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舉行的一項慈善瑜伽活動。(海峽時報)
一個經濟體的行善指數,反映出一個社會的善行是否受到鼓勵,能否順利展開,「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不可或缺。
受該研究調查的新加坡社會服務組織中有80%得到了政府資助,位列第一,其後是台灣和日本,獲資助的比率分別為68%和66%。這個排名似乎也跟一個經濟體的富裕程度有關。
新加坡的國家外匯儲備和個人平均收入多年來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國家整體的「行善氣候」本就應該在國際上有優異表現。

貧窮國家的行善事業,須靠國際組織援助。(法新社)
矛盾的是,更需要慈善事業幫助的是貧窮國家,但它們的政治領導權又往往落在貪污腐敗的竊國者手中。因此,行善事業得靠國際組織伸出援手。
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聯合創辦人兼主席陳啟宗說,三分之二受疫情影響而被迫陷入貧窮線的人位於南亞、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意味著這些經濟體急需公益慈善的支持。
例如近日宣告破產、人民造反、曾經是印度洋一顆明珠的斯里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如喪家之犬,留下一個爛攤子,日前倉皇逃來新加坡。
當全國人民得不到溫飽時,它最迫切的問題就已經超越慈善事業的範圍。國際機構的援助幫得了一時,幫不了一世。斯國目前最需要的是一個有能力恢復經濟的有效而廉潔的政府。
所以,這個「行善指數」似乎只適合用於評估較富裕的國家和社會,貧窮國家面對的是更大的經濟問題。
此外,起起落落的冠病疫情給較已開發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同的挑戰,個人和企業受到沉重打擊,政府也把重點轉移到撥款補貼個人與企業。與此同時,社會上的慈善更須要加碼,弱勢群體的處境更須要額外的關注,社會服務組織的擔子就更重了。
69%的新加坡社會服務組織接受企業資助,亞洲平均水平則為54%。本地企業資助占企業總預算的約11%,同比2020年的17%略有下降。企業與政府的行善夥伴關係越來越密切,這是新加坡能在「行善指數」高居榜首的關鍵因素。

2022年7月14日,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最前)參與內政科學據的年度義騎籌款活動。(海峽時報)
7月14日,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和10名政要和國會議員到東海岸公園雨中騎車,參與一項為弱勢家庭籌款的活動,支持他們購買翻新後的筆記本電腦。
這是由內政科學局(HTX)舉辦的年度義騎籌款活動,既鼓勵旗下的員工積極運動保持身體健康之外,該局今年也同非盈利組織「工程向善」(Engineering Good)合作,將預計籌到的50萬元捐給該組織以推動數碼化。
新加坡政府以一對一補貼政策,鼓勵企業和社會組織籌集善款和活動基金,政治領導又以公眾看得到的實際行動參與其事,是個「政治非常正確」的表態。
新加坡式的行善是一門現代管理和政治學問,這是「行善指數」所沒有告訴人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