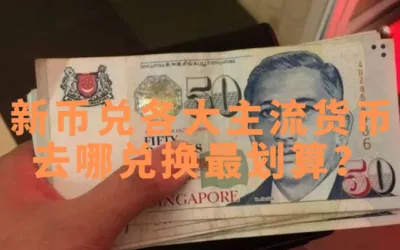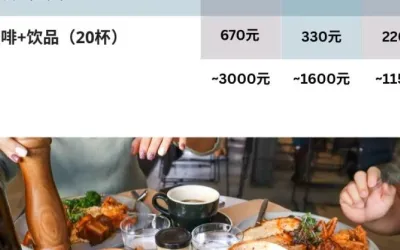“刚刚踏入意大利,他们便陷入了席卷全国的音乐激情。这种激情在平民百姓中跟在精英当中一样炽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音乐笔记》中如此描绘18世纪的意大利:“小提琴、乐器演奏者和歌声让我们在大街上为之驻足。你可以听到鞋匠、铁匠、木匠在演唱一首咏叹调,分成几个声部,有板有眼,品味纯正。”
当音乐从殿堂走上街头,艺术便重新回到了生活的怀抱。此刻,歌声不仅填充了城市的空间,更展现了一个民族的激情与梦想。

街头艺人因疫情消失街头,一年多来,他们转到线上继续施展唱作才华,或为热爱演艺,或为补贴生活,更为传达艺术源于生活的理念。
在21世纪的新加坡,繁华都市里同样有充满才华与激情的表演者。根据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资料,全国目前约有300名获得认可的街头表演者,在80多个指定场所表演。他们当中约半数为35岁以下,最年长者为83岁,最小的只有11岁。
然而自去年3月26日起,街头表演活动因疫情暴发戛然而止。在这漫长的16个月里,他们生活得如何?是否依然坚持着表演的激情,或是另谋他业?
我们采访了五名本地街头表演者,他们当中有人13岁开始就在街头表演,曾代表新加坡参加英国爱丁堡的街头艺术节;有人飞跃太平洋在更广袤的土地上以音乐行旅,觅得终身伴侣;也有人年过半百才走上街头,以一首又一首歌撑起一个家。

去年12月,艺理会首次推出实体街头表演试行计划,在确保安全距离的情况下让部分街头表演者重返“舞台”。(艺理会提供)
梁斯琨∣一把古筝养出两名高材生

疫情居家,梁斯琨研发出可弹七声音阶的新制古筝。(李健玮摄)
30年前,梁斯琨(57岁)还是一名书画装裱师,弹古筝是他自中学以来的爱好。1990年代末,书画装裱行业逐渐没落,梁斯琨开始以教古筝为主业,开班收徒,也在中学里教课外活动团体。
然而近年来,学校课外活动的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校每一年都会重新招标。从原来在三所学校任教到只剩一所,梁斯琨作为一个四口之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倍感压力。
2016年,52岁的梁斯琨第一次走上街头表演古筝,一开始还很放不开。不过几周下来,来看的人渐渐成了熟客,时常攀谈起来,让他觉得轻松不少,也更有意思。

梁斯琨是第一批参加街头表演直播试行计划的街头表演者之一。屏幕下方有可以捐款的QR码,但是效果不比在现场。(艺理会提供)
“有时候遇到真心喜欢音乐的路人,可以站在那里听两三个小时,心里是很有满足感的。”他透露说:“在户外表演不仅可以赚到一些捐款,也会因此招到更多学生,有时还会收到一些演出邀请,通过这些渠道增加的收入大概可以占到三四成。 ”年轻时热爱书画的梁斯琨曾考入当时的南洋美专,却因为家里付不起学费未能如愿。因此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无论如何要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
让梁斯琨倍感欣慰的是,儿女各自学有所成。女儿正在美国著名的密歇根大学攻读地质学博士,儿子就读于新加坡管理大学,明年即将毕业。不过他认为主要还是太太的功劳,没有她在家中的细心照料,孩子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虽然今年已经57岁,儿女即将独立,梁斯琨丝毫没有退休的打算。他表示,在社区表演是件快乐的事。如今没有了压力,可以更从容地享受生活和音乐。
疫中沉淀 研发新乐器

路人拍下梁斯琨演奏的视频,配上歌词后发在面簿上。(受访者提供)
虽非科班出身,梁斯琨也曾求教于熊岳等古筝名家,琴艺不俗。在街头表演时,除了流行歌曲,偶尔也会碰到有人点一首古曲如《战台风》,梁斯琨也能应对自如。
从去年4月起,告别“舞台”的梁斯琨在家琢磨起了手中的乐器。传统的古筝采用的是东方五声音阶,在他构思设计后,亲手打造了一台可以演奏西方七声音阶的古筝,正准备申请专利。

梁斯琨琴艺不俗,除了演奏流行歌曲,对传统古筝乐曲也应对自如。
今年6月,艺理会推出街头表演直播试行计划,每季度(三个月)一场。梁斯琨作为第一批艺人登场,从演播室里通过网络直播表演。除了艺理会提供的津贴,公众也可以通过QR码的形式捐助或打赏。

今年6月起,艺理会推出街头表演直播试行计划,让街头表演者通过直播方式与观众见面互动。(艺理会提供)
女儿在美国读博有奖学金,其余的三口之家在这段时间靠着自雇人士的津贴和教琴收入还可以维持。此外,梁斯琨还学起了吉他和唱歌。他说:“既然难得有空闲,就多提升自己的技能,多学些大家喜欢的老歌,粤语歌,以后肯定还会用到。”
余紫薇∣时代落幕 余音犹绕梁

余紫薇虽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唱歌,但她还是喜欢现场互动的真实感。
余紫薇(55岁)是一名家庭主妇,从学生时代参加各类歌咏比赛起,唱歌便是她一生的挚爱。
每次出国旅行,余紫薇看到街头上自由放歌的街头艺人,心中都会有所向往。她也曾是一些乡村俱乐部的会员,喜欢在舞台上一展歌喉。“可是近几年来,很多俱乐部都相继关门,我们很多热爱老歌、爵士歌曲的人一时没有了舞台。”余紫薇的语气中难掩落寞。
为了把这份热爱延续下去,余紫薇和弹吉他的朋友组成二人组,在露天场合为公众表演。家人也很支持她,老公有时会开车载她去表演的地方,孩子有时也会到现场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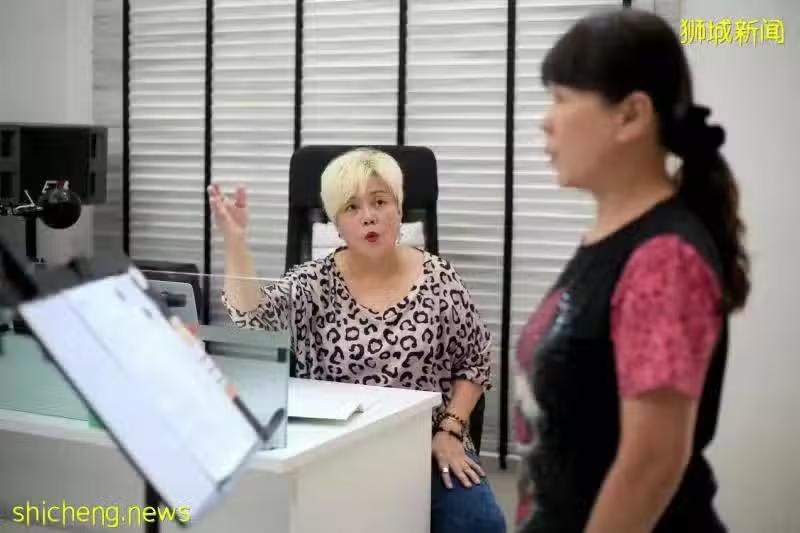
对余紫薇来说,看到别人掌握正确的歌唱技巧非常有满足感。(龙国雄摄)
余紫薇比较喜欢的表演地点是金沙酒店附近的雾霭走道(Mist Walk),那里的游客比较多,互动性更强。收到游客的点歌她会很开心,因此除了自己擅长的英语老歌、爵士等风格,她也学习周杰伦、林俊杰等的华语歌曲。
“虽然我出来唱歌并不是为了赚钱,但是得到别人的认可、关注是一件开心的事。”余紫薇还注意到,一般认为出手阔绰的洋人其实并没有想像中的大方,除非是遇到特别喜欢的歌曲。从中国来的游客,则多数都比较慷慨。
教乐龄唱歌 收获双份快乐

疫情居家之后,余紫薇积极尝试新科技,使用网络直播平台开唱。(龙国雄摄)
自从疫情居家开始,余紫薇尝试在网络直播平台(Twitch)唱歌,逐渐在个人账户下积累了数百个粉丝。
不过她认为:“虽然粉丝数量看起来比现场观众多,但是那种现场互动的真实感是无法取代的。”
从去年开始,余紫薇把更多精力放在教乐龄人士唱卡拉OK这件事上。看到老人家在唱准音、唱高音这些技巧上获得进步而感到快乐,她自己也同样收获满足。
余紫薇年轻时参加过卡拉OK比赛,不过当年勤奋的她以错误的技巧苦练,虽然赢得比赛,却在赛后失声,甚至动了手术。之后她曾系统地阅读资料,找老师学习发声技巧。因为亲身经历过这样的挫折,她不希望有同样热爱唱歌的人重蹈覆辙。
因为很多学唱歌的都是退休后的老人,余紫薇也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些费用。不过因为疫情的原因,余紫薇的家庭经济状况也并不乐观。
余紫薇并没有像其他自雇人士一样获得政府津贴,因为她家的地址是有地房产。但事实上,他的丈夫因疫情失业,现在从事房地产经纪;儿子是健身教练,收入也受收紧政策影响,只不过还没结婚与父母同住,同样因住家地址原因无法获得津贴。 她希望政府的政策能够再细致一些,可以根据各户情况酌情考虑,而不是一刀切。
Elsa Faith∣因音乐结缘 以音乐行旅

Elsa擅长吉他贝斯,喜欢演唱和创作摇滚类音乐。(邬福梁摄)
Elsa Faith(39岁,本名Siti Noor Firdaus Binte Akmat)也认为,很多街头表演者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热爱和快乐,但在本地却容易被人误解。
她出生于一个音乐氛围浓烈的马来家庭,从小随两个哥哥弹吉他,学唱歌,去世贸中心(现怡丰城)或其他演艺场所表演。在从事行销工作之余,她依然保持着唱作的热情。她擅长的乐器是吉他贝斯,喜欢演唱和创作摇滚类音乐。
2006年,Elsa在网络博客结识了一名志趣相投的美国人。在美国国庆日的前一天,她飞往美国,两人在浪漫的国庆烟花中相遇。那年冬天,他们结婚并开始长达13年的音乐行旅。
两人长居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几乎每年都会开车南下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演出。他们也会沿途表演,向人推介自己创作出版的唱片。
考虑到父母年迈,Elsa与丈夫在2019年一同回到新加坡,与家人团聚。他们注册成为街头表演者,继续燃烧激情。
她最爱的表演场合是哈芝巷,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我的音乐风格和哈芝巷的气质非常搭。那里除了有喜欢我音乐的听众,也有志同道合的表演者,那里就是属于我的甘榜。”

Elsa(右)与吉他手丈夫在美国加州的表演。(受访者提供)
线上演出吸引跨国界音乐人
在过去一年里,Elsa与音乐人Lynn Dresel组织的We Are Music (SG)在面簿和YouTube举办了几场线上公开麦(open mic,任何参与者都有机会上台表演)和音乐节,吸引本地和区域内的许多音乐人参加。
Elsa平时也会帮弟弟打理自家经营的机车周边用品生意,包括赛车服、配件等。店面就设在一家机车修理店的二楼,车手来维修机车时一般会上楼光顾。因为赛车与摇滚在相近的文化圈中,Elsa有时也会在店里弹吉他,唱歌,与顾客聊天。
不过,她最怀念的还是哈芝巷,想念那里的人,想念在那里的歌声和欢笑。
维格纳什∣ 架起社区与艺术殿堂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