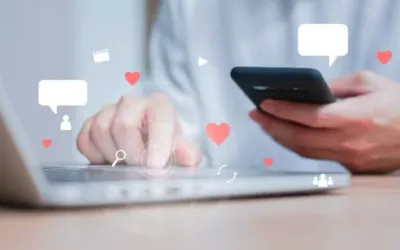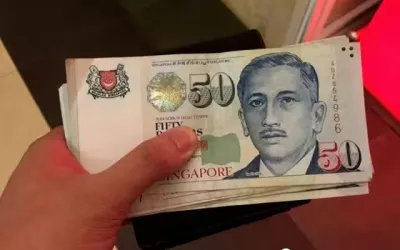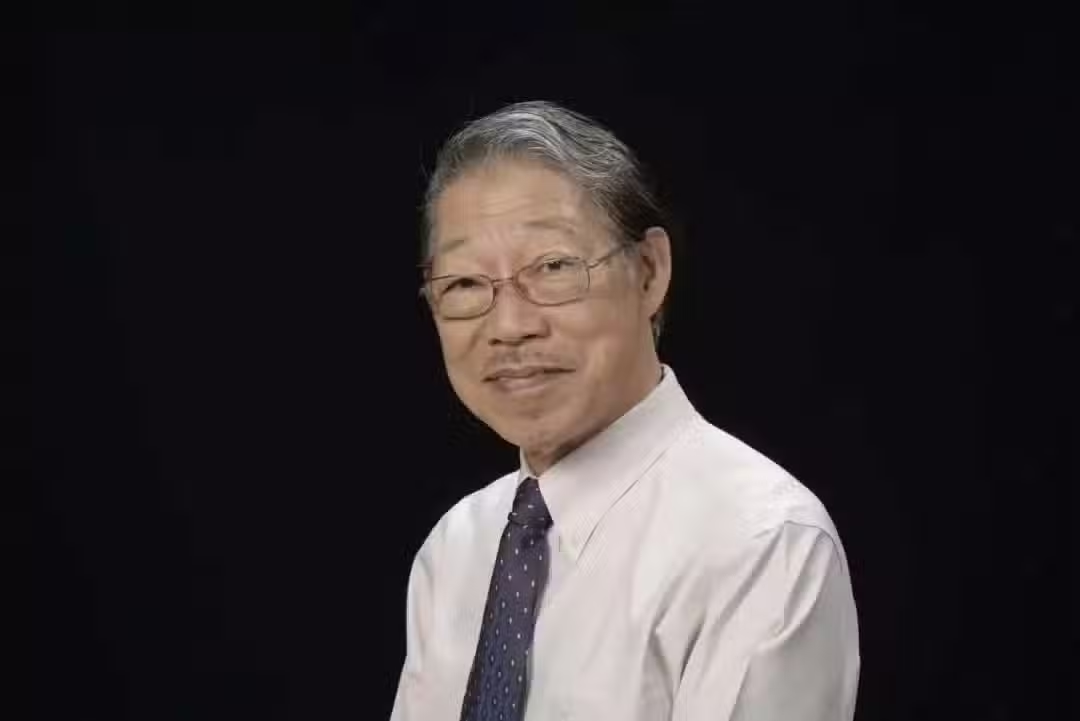
▲本文作者郭振羽
前言
2013年4月,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宣布成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到2023年正好滿十年。又過五年,斥資1億1000萬元新建的文化中心於2017年正式開幕。前總理李顯龍為文化中心主持開幕儀式時強調,一方面希望文化藝術領域的人才,能貢獻才能,一起傳遞文化薪火。同時也強調文化中心所推廣的文化,除了傳統和現代中華文化,也將涵蓋新加坡獨特的華族文化。總結而言,中心的任務是「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縱觀華族文化中心過去這五年的活動,不論是演出、展覽、講座,或是座談,大致都是環繞文化的傳承和創新,一方面保留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另一方面鼓勵創新,努力尋求建立具新加坡特色的新加坡華族文化。
其實不只是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此地的宗鄉會館無不以保留文化傳統,服務鄉親為宗旨,同時舉辦活動,吸收年輕一代會員,傳遞「文化薪火」。譬如揭陽會館在九月間聯合各潮屬會館,舉辦潮州習俗為青少年舉辦的「出花園」成年禮。2023年六月,廈門公會慶祝八十五周年會慶,舉辦盛大的國際研討會,定名為《閩南文化在新加坡》,有超過五百人出席一整天的學術討論活動。此外,諸大會館也先後舉辦盛大文化展,如福建文化節、潮州文化節、南安文化節等;也多次召開跨區域的國際懇親大會。這種種活動都呈現華族方言文化的活力和承傳。
源自神州的中華文化由原鄉遷移到新土,為適應新環境,要求生存求發展,必須做文化調適,以原鄉文化為資源,並吸取在地新資源,這中間有傳承,也有創新,逐漸呈現本土特色。
而制約文化調適的因素包括地理和社會文化條件。
就以最基本的地理條件而言,新加坡地處熱帶,周圍環海,和神州大地溫帶平原是一對比。以2016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遺名錄」的廿四節氣為例,原是中原農耕社會四時運作所遵行的曆法,具有指導農耕活動的實用功能,之後演變附加歷史文化意義。在南洋赤道驕陽下,節氣如驚蟄、霜降、小雪、大寒已經沒有氣象學上的意義;在完全沒有農耕操作的新加坡,更沒有實用價值。但是身處南洋的華人還是清明掃墓、冬至吃湯圓,其意義在於保留華夏文化傳統。再譬如「白露」,新加坡當然沒有「白露為霜」,大家記得的是充滿詩意的「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換句話說,節氣的文化因素被保留,甚至發揚光大,保留了原鄉的文化記憶;一般人已經不了解,也不在乎節氣原來的實用意義了。
在社會因素方面,最重要的是人口結構。位居赤道的海島新加坡,自開埠以來就是個多元民族構成的移民社會,在文化、語言、宗教、習俗各方面,都呈現多元格局。地理上又是個多方商賈彙集的港口,多元互動交流是常態,彼此相互影響,本身就是一「文化雜糅」(cultural hybridity)的典型範例。
此外,200年來,新加坡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在文化以及政治方面留下大不列顛不可磨滅的遺蹟。自1965年獨立以來,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經歷強勢政府治理下的條規和政策(如語言、教育、傳媒)和政治文化,深入生活。這些特有條件也反映在新加坡文化內涵之中。
南洋、南洋風和南洋畫派
近年來,新加坡政治領袖和華社領導一再關注尋找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強調新加坡華人已經建立特殊的文化面貌。此時此地關注我們的特殊性,究其原因是反映現階段對新加坡社會認同的集體焦慮(collective anxiety)。為了要彰顯新加坡華族文化有異於其他海外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的文化特色,有其難度,因為東南亞,特別是新馬兩地,地理景觀相似,同樣經過殖民時代背景,所謂華族文化特色,各地諸多相似之處,要特加新加坡獨有標籤,不免常有爭議。
新加坡開埠200年,逐漸發展為多元民族人口彙集的國際大都市。多元族群經過多年的交流互動,在文化方面必然相互影響,這是新加坡社會豐富的文化資源。同時,我們也深受周邊地區多元文化的影響。當我們審視新加坡華族文化如音樂、舞蹈、戲曲、美術、文學、語言,以至於飲食、服飾、建築等等,處處呈現來自友族以及東南亞各地的多/異文化元素。所謂「南洋風」,其來有自。
「南洋」是我們極為熟悉的名詞,帶有中國本位的意涵。廣義而言指南中國海附近的東南亞地區,包括中南半島和馬來群島(包括新、馬、印、菲);狹義而言,在歷史上,南洋指的是馬來亞地區,即是今日的新馬地區。而我們身在新加坡,更習慣性認為南洋就是新加坡。
回溯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海外華人(中華)民族意識萌生,「僑居地」和「祖國」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交流頻繁,中華文化在南洋充分發展,是新加坡華族文化奠基時期。諸多重要華校、華報、華族社團於此期間創立,由新加坡擴及南洋各地,奠定了南洋以及新加坡華族文化根基,形成所謂的「南洋文化圈」。
由「南洋風」衍生的文化,包含了南洋畫派、南洋建築風格、南洋服飾、南洋風味菜式等等,甚為豐富,其影響力遍及東南亞以及閩粵僑鄉。
「南洋風」所呈現的當然算是新加坡華族文化特色,但卻未必是新加坡獨有的。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前,基本上新馬不分。以食物為例,有關諸種南洋食品的原始出處,近年來兩地之間不乏爭議,譬如肉骨茶、撈魚生,出自何時何地,爭議不斷。再以「海南雞飯」為例,雖然以海南為名,卻是海南所無,遠在紐約卻還吃得到「新加坡雞飯」。在紐約和香港還有「星洲炒米粉」,倒從來沒有人指稱為獨特的新加坡食物。由此看來,諸種「標籤」多是人定的,爭論出處難有定論,也沒有意義。
1952年陳文希、劉抗、鍾泗濱、陳宗瑞四位新加坡畫家結伴到印尼峇厘島旅遊寫生創作。次年,四人在新加坡聯合舉辦轟動一時的「峇厘之旅作品展」,展現南洋地區的藝術風貌。1980年,鍾泗濱著文主張建立「南洋畫派」。之後多年,有關南洋畫派的定義和定位,討論不斷。近日更出現「風」和「格」之辯,也開始有學者探究「南洋畫派」究竟為何,甚至於是否還存在。
而當新加坡就此爭辯不已之際,鄰近的馬六甲在2016年成立南洋畫院,標榜「新南洋畫派」,聲稱馬來西亞「華裔畫家在繼承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又結合了南洋地區其他民族的繪畫理論形成了風格獨特的南洋畫派」。2019年2月6日,自稱為馬來西亞「當代著名(南洋派)藝術家」的謝忝宋登上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大螢幕,展示其藝術創作,聲勢浩大,背景不詳。同年7月,馬來西亞畫家戴蕾珍在馬六甲舉辦畫展,以「南洋畫派第三代傳承人之一」自居。由此諸種跡象看來,關於馬來西亞有意以「南洋畫派」申遺的傳言或許不假。
此處討論「南洋畫派」的重點不在何謂南洋畫派,何謂南洋風,以及「風」和「格」的定義內涵,更無意參與馬來西亞畫家作為「南洋畫派傳承人」之辯,此處要強調的還是在文化特殊性的定位。顯然,新加坡不能以1950年代的「峇厘之旅作品展」衍生出的「南洋畫派」或「南洋風」視為專有。馬六甲方面強勢爭取以「南洋畫派傳承人」自居,看來南洋畫派「身世」之謎,一時還難釐清。當年新馬一家,同屬馬來亞;如今新馬分家,各自為政,也只能和馬來西亞共戴「南洋」一冠了。
民間信仰的引申:從七月普渡到慶贊中元
如果連「南洋文化」都是新馬不分,不能視為「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那我們要如何尋找我們專有的新加坡華族文化?
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曾玲教授2023年6月應新躍社科大學之邀,發表專題演講,題目是「從七月普渡到慶贊中元: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創造」,深入淺出分析新加坡華族社會盛大舉辦「慶贊中元」嘉年華的背景和文化意義,可以作為新加坡獨特華族文化的一個實例。
曾玲教授研究新加坡中元節活動多年。根據她的研究,最早有關本地中元普渡的報道出現在百年前的《叻報》。1888年9月8日《叻報》報道在中元節期間,「盂蘭之會本坡向最盛行。今已屆仲秋,則普渡之事已畢。」
依曾玲的研究,中元節慶的新加坡在地化,主要發生在1965年新加坡獨立之後。建國後,「新加坡面對諸如國家認同之建構、社會重組與城市重建、多元種族、宗教、文化和諧政策的制定等等。」新加坡中元節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演化進程。
曾玲分析中元節在新土的文化創造,集中在三特色,為原鄉所無,而在獨立後的新加坡社會提供重要功能。
第一是出現在華族社區的「中元會」,成為常年主辦慶贊中元活動的非正式組織機構。曾玲指出,中元會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遍布新加坡全島各處;建立中元會的組織團體包括華人廟宇、華人社團、新鎮社區、各行業、工廠與商場,甚至於政府部門、警察局、移民廳、地鐵站、巴士總站等。此類組織均為非官方,無需登記(在新加坡極為少見),不具法律地位,但自有其約定俗成的規則和約束力,為眾所遵循。曾教授強調,「中元會的出現,適應了建國後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社會重組與加強社會凝聚力的需要,已經成為當代新加坡聚合人群、凝聚社會認同的最基層的民間組織。」
目前,新加坡人普遍的慶祝方式是基於各社團機構以及鄰里組成的中元會,每年選出一位爐主,由頭家爐主與理事主持中元會事務,向會員收月捐等。中元節一到,這些月捐便用來購買祭品。拜祭完畢後,所有祭品均分給會員,每人一份。擔任爐主是一大榮譽,自然成為地方領袖。
第二個特色是多元的酬神方式。新加坡禮讚中元承繼傳統的的「酬神戲」,逐漸轉換為娛樂大眾的「中元歌台」。傳統的酬神戲主要為了娛神或答謝神祇,同時供善信觀賞,與民同樂。1970年代之後,電視逐漸普及,方言戲劇相對沒落,傳統酬神戲對年輕一代失去吸引力,現場演出出現觀眾寥寥無幾的現象。中元會為吸引年輕人參與,開始引入歌台演出,逐漸取代傳統的酬神戲,到了新世紀愈為流行。根據《新明日報》報道(2016年9月4日)「萬人芽籠爭看歌台。歌台鬧哄哄,大戲冷清清」,據報道,每晚各地歌台達四十處之多,每晚歌台聘金可高達萬元!(《新明日報》1996年8月13日)觀眾竟達萬人以上!可謂萬人空巷。
新加坡普贊中元的第三個特色是「標福物」。中元會通常會在公共場所如大草地舉辦。早期中元會擺放酒席中,最中間的一桌放空留給「好兄弟」。參與者每月向爐主捐出一筆錢。這筆費用隨後用來購買拜祭「好兄弟」的供奉品,之後也會在參與者之間分配。
「標福物」也在中元會中同時舉行。中元標福物,不一定是高價值物品。這些物品通常是受過道士「開光」的「福物」,具宗教意涵,也是新加坡慈善團體籌款的重要來源。根據曾玲教授的統計,單單在1996年,全國腎臟基金經由700個中元會共籌到善款100萬元;同年廣惠肇留醫院也經900多個中元會籌到48萬元款項;大眾醫院則經由560個中元會籌到款項11萬元。民間酬神辦慈善的財力不可忽視。
依曾玲的分析,中元標福晚宴兼具多種功能,是提供一個持續整個農曆七月、涵蓋全新加坡各界與全島各處的社會大舞台。匯聚多元功能的中元標福晚宴,遍及新加坡全島。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也樂於參與,與民同樂;它兼有社會公益慈善功能,同時向非華族開放與促進國家的多元種族和諧。此一特色或是新加坡慶贊中元獨有的多民族共慶(華族)中元一大特色。
結語
150多年來,新加坡的華族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就穩定地占四分之三左右,也是中港台之外唯一的華人占多數的國家。因為這樣,在這裡的華族人口始終占的是主導地位,相當能夠保留原鄉的文化特色。我們是中華之外,又在中華之內。中華是脫不去的標籤。
這篇短文要討論的主題是尋找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結果好像還找不到答案。新加坡獨立到今年59年,在一個歷史長河裡面太短了。只能靠點點滴滴的努力,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孕育出獨特的新加坡華族文化。目前我們更關心的應該是當今華語華文水平的低落,當務之急是如何推動保留文化之根。
新加坡的華族文化離不開大中華文化圈,繼續受到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影響。而今中國崛起,對新加坡的華族文化自然有所衝擊。這過程中,涵蓋「中心」跟「邊陲」的互動和轉換,也涉及多元身份認同的流動。這是新加坡華族文化先天存在的「雙重性格」,兼有源自原鄉華族文化的共性,以及作為「新土」的新加坡文化的特性,也是新加坡華族文化寶貴的資產。出現於「新土」的文化創新,也已成為文化中華的一部分,可以豐富其文化內涵。
另一方面,就在新加坡本身,華族文化跟非華族文化——馬來文化、印度文化,在差異之處外,是不是有新加坡文化的共性出現?這其間文化認同跟身份認同交錯重疊,需要深入觀察。
作者簡介:
郭振羽教授於1990年至1995年間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大眾傳播系創系主任。
1992至2003年間擔任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創院院長;2003年籌劃成立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並於2003年至2005年間任創院(署理)院長。
2008年加盟新躍大學(現稱新躍社科大學)任學術顧問;2012年任「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
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終身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