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52年英國派駐印度的總督(當時新加坡在印度轄下)通過以出生地為原則的國籍法,更進一步分化峇峇華人與新客華人的距離。峇峇華人在法令下成為英國臣民(British Subject),他們開始自稱為海峽華人 (Straits Chinese) 或英籍華人 (British Chinese) ,效忠英女皇,稱英國為「祖家」(天福宮重修碑文里說的「祖家磚」指的就是英國磚)。言必稱:「我是英國臣民,白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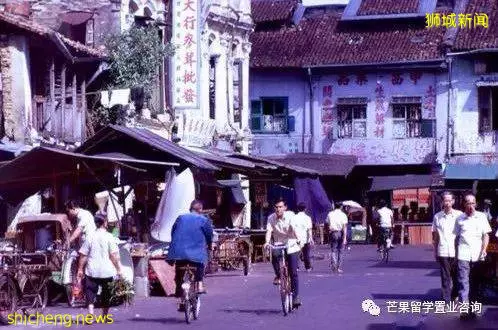
新客的大量到來當然沖稀了峇峇在華人人口的比重並超越他們成為主要的華人族群,不過峇峇華人還是這個時期新加坡貿易的主要掌控者。一些出類拔萃的新客通過與峇峇聯姻的關係,爬上了上層社會的台階,峇峇家庭也喜歡引入有幹勁的新客女婿以保持家族的生命力,這種互動造就了另一種類型的社會新貴,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佘有進、胡亞基等。

游離在英國祖家和唐山之間
由於「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這種西方的概念還沒帶進中國,這些華南新客當然也就沒有所謂的「國家」意識,他們最大的公約數就是「唐人」的概念,內部又因為宗鄉觀念而分為不同的方言幫,可說是一盤散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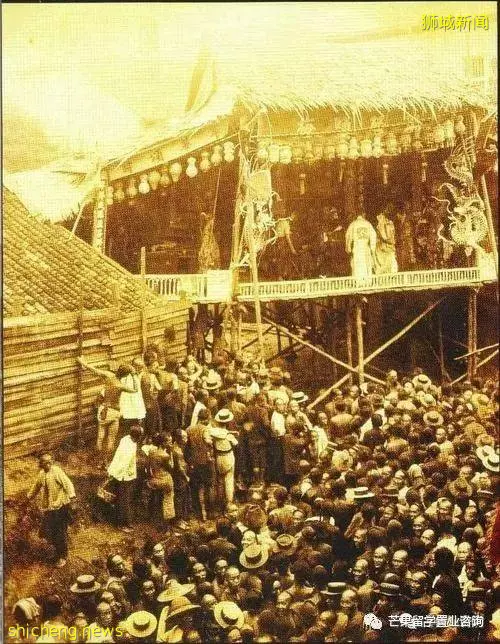
1860年後清廷對海外華人的態度開始轉變,從不聞不問轉為開始接觸並採取籠絡的手段,1877年更在新加坡設立「海門領事館」,委任新加坡居民胡亞基為領事,統管海峽殖民地的華人事務。這種轉變最大的原因就是鴉片戰爭後的割地賠款造成國庫空虛,需要吸取海外華人的資金來填補,採取的手段就是把捐官買爵的「鬻官制度」推廣到海外。

清廷態度的轉變以及「鬻官制度」不但為清廷增加國庫的收入,也對新加坡峇峇社會產生影響,並使他們的向心力再度向「唐山」傾斜,1869年章芳琳成為第一個獲得官銜的新加坡峇峇僑領。從一張1899年新加坡華社為慶祝維多利亞女皇登基50周年而向總督金文泰 (Cecil Clementi) 捐贈英女皇的大理石雕像,在總督府前舉行揭幕典禮的合照就可以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三十四位新加坡華人商界領袖在佘連城領導下一律穿著清朝官服,頭戴花翎官帽與總督等英國官員合影。

這些以峇峇華人為主的僑領是不是全部都是通過鬻官而得到官銜或者只是為了虛榮而如此打扮就不得而知,不過它說明了一點就是華人傳統光宗耀祖的思想在這些峇峇心中還是根深蒂固,他們試圖在效忠英國「祖家」和向「唐山」傾斜之間尋找平衡點。

新加坡國家意識的建構與華人身份認同的重構
獨立之後的新加坡面對艱難的國家認同的建構問題,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雖然占絕大多數,不過還有大約15%的馬來人及9%的印度人以及少數的其他種族,他們構成新加坡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過去共同的殖民地統治和相同的移民經歷,而不是相同的種族、文化或宗教背景。

新加坡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除了實施國民服役制度、在學校進行念「誓約」的儀式等等,最大的舉措就是把獨立前四大源流的教育統一在一個以英文為主導的教育體系之下。

希望下一個五十年,新加坡能成為一個既可「安身」也可「立命」的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