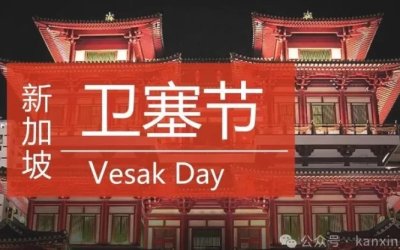1963年,南洋大學迎來了「後陳六使時代」。1963年9月16日,馬來亞聯合邦、沙撈越、沙巴和新加坡,共同組成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成為這個新國家的一個州。政治的驟變把陳六使卷進旋渦,9月22日晚,尚未組閣的新加坡政府宣布褫奪南大理事會主席陳六使的公民權。三天後,為南洋大學奉獻了整整十年的陳六使,向理事會辭去主席一職。

陳六使
陳六使時代與後陳六使時代有著巨大的差異,在這一點上,我們更能體會出陳六使為了南洋大學長期盤恆於政商學三界的不易。陳六使辭任後,1963年10月5日,大學理事會不得不接受指令改組南洋大學。到了1964年7月10日,南大臨時校內行政委員會舉行移交儀式,接受校長印信及各項重要文件。從此之後,另一股力量參與進南洋大學的管理,我們可以把後陳六使時代稱之為「艱辛時代」,因為相比之下,陳六使時代的南洋大學雖然遭受著種種非難,但整體還是意氣風發,到了後陳六使時代的南洋大學,即使還有很多教職員工,努力捍衛著這所大學的「初心」,1970年,時任南洋大學校長的黃麗松博士撰寫了《在發展中國家裡成長的南洋大學》,他說,南洋大學的優勢在於「一開始就認定以東方文化為基礎」,在他的任期里,南洋大學的學術研究層面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南洋大學「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氣氛,在1963年之後就沒有消失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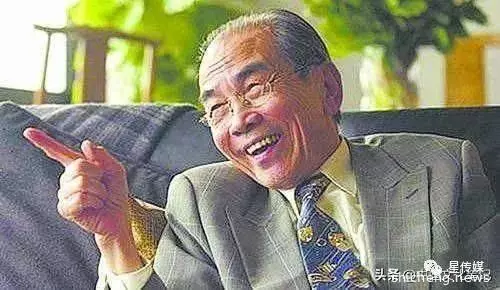
黃麗松博士
離開南洋大學之後,陳六使有時還會對南洋大學的校務發聲,但今非昔比。雲南園已經不是當年的雲南園。他眼睜睜地、沉默地,看著自己當年的理想,漸行漸遠……
1964年8月,嚴思曾寫了一首《在寒星蕭索的夜晚》,歌詠早期南洋大學的地標之一「水塔」:
「我要走了,走了……/在寒星蕭索的夜晚裡我要想你/用不變的心/用不變的愛情/在今後火海刀山的日子裡啊/水塔,願我們/在祖國蒼茫的天空里/發出勇猛的力量……」
讀起這首詩,我們會想,嚴思筆下的水塔,真的只是那座塔嗎?陳六使不就是長久屹立於南洋大學的水塔嗎,他的信念,他的「使命」,始終在提醒南洋大學的千萬校友們,你們所應該傳承、應該奮鬥、應該護衛的究竟是什麼?是中華文化的血脈,是民族文化的根基……
有一些南洋大學學生,因為各種原因對陳六使抱有有趣的敵意。1966年,一位南洋大學校友聲稱,陳六使承諾為南洋大學捐出500萬元,卻還拖欠250萬元;福建會館認捐的60萬元還欠40萬元;《南洋商報》承諾給大學100萬元,兌現的卻只有9萬4千元。這成為質疑陳六使「背信」的有力證據。這位東郭校友,真可謂算得一筆好帳。但陳六使在捐款時就已經說明,他認捐的數額並非一次性捐出的,另外,1963年起,南洋大學已經不再是那個陳六使和福建會館,以及華人社會所理想的南洋大學。它應要求不斷改組,它的發展方向模糊不清,它拿什麼來要求陳六使履行承諾呢?
一艘大船,緩緩調轉了航向。
1972年7月29日 南洋大學舉行第十三屆畢業典禮。這是一屆特殊的畢業典禮,因為南洋大學研究院的第一屆博士及碩士正式畢業。在黃麗松校長的領導之下,南洋大學證明了自己的學術水平。但是此時的陳六使,即將走完他76年人生之路。
一個半月之後的9月11日,76歲的陳六使因心臟病突發不幸去世,新馬各界深感悲痛。南大校友敬獻的輓聯上寫著:「含辛茹苦,創南大,一擲萬金無吝色;白手起家,辦教育,千錘百鍊育英才。」包括南大師生在內的6000人為陳六使送行,在陳六使的靈柩上,覆蓋著南洋大學校旗。16年前,正是陳六使主持了升旗儀式,宣布南洋大學開學。那時候的他和那時候的南洋大學一樣意氣風發。16年後,斯人已逝,空留迴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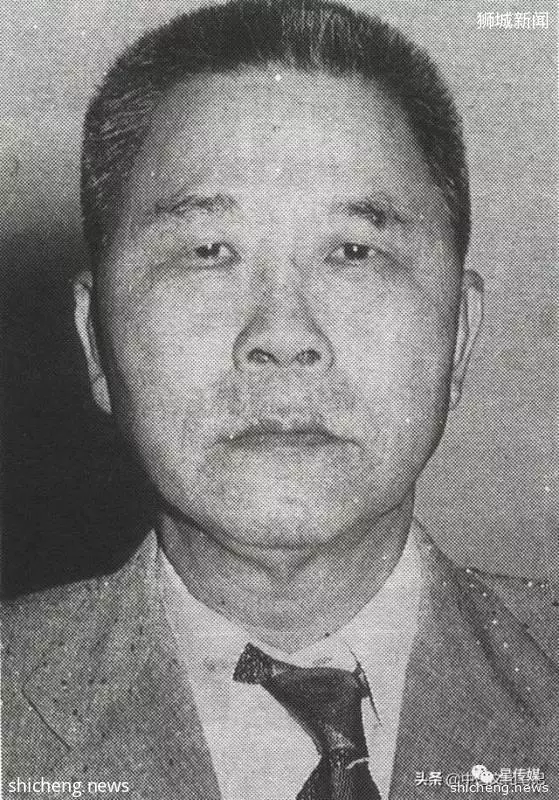
作為一個橡膠商人,他無疑是成功的,但他最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商場,而在於這所寄託百萬華人希望的南洋大學。如今也許很少有人還記得曾經叱吒風雲的益和樹膠公司,但只要南洋大學的牌坊還豎立在雲南園,人們就一定會記得他這位南洋大學的創辦人。
我們可以回憶起那些特殊的「陳六使」時刻:
陳六使六十壽辰時,南洋大學學生會致信說:
「正當華文教育遭受極大迫害之際,先生奮力號召南洋各界人士起來創建南洋唯一華文大學(事實上也是海外華人有史以來自己創辦的第一間規模完備的大學),以維護及發揚中華文化,在這偉大的工作中,先生始終以任勞任怨的精神,積極領導各界人士,克服重重困難,共同為創造南洋大學而努力,南洋大學有今日,光生之功績是不可估計的,先生之令名將與南洋大學同垂永遠。」
1953年7月26日中午12時,執委會主席陳六使在雲南園主持大學築路工程動土典禮,他以歡快的口吻說:
「今日是南洋大學動土之期,兄弟在此主持,感到非常興奮,吾人已在此播下文化種子,吾華人之文化在馬來亞將與日月同光與天地共存,中國人之文化是不會被消滅的,吾人在馬之文化,正如馬來亞一樣應該永遠地存在。去年兄弟鑒於華人文化存有危機,不得不極力提倡創辦南洋大學,目的在使吾人之文化能在本地永遠持續,各位今日看到此地帶系一片荒野,但此地實系中華文化在此生根之處,永遠存在,永不消失。」

中華文化將在南洋「永遠存在,永不消失」,而陳六使「之令名將與南洋大學同垂永遠」,這是多麼美好的期待,也是多麼美好的祝福,它寄託著多少信心。陳六使已逝,南洋大學已殞,但他的貢獻將始終銘記在新加坡的藍天碧海,與日月同光。
陳六使的去世,仿佛暗示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六十年代初時,南洋大學學生們看到校園中的相思樹時,寫的詩是這樣的:
「雲南園的花朵已怒放了/沐浴在金黃色的清晨里/不知多少次我挾著書本走過去/ /相思樹的青葉還在滾著珠水 /垂彎著腰歡迎我的到來/我常常漫步在相思樹邊的小路上。」(《我的歌呵,你從雲南園飛出去》,作於1961年)
到了七十年代,關校的陰影之下,南洋大學的學生們再看到相思樹時,他們寫的詩是這樣的:
我們有無盡的相思/一陣微風,葉與葉拍擊/聒噪著,以我們的語言/在這樣黯然,光芒微弱的年代。(南子《相思樹》,作於1970年代)
1973年底,南洋大學被要求停止在大馬招生,生源愈發萎縮。1975年,原教育部長李昭銘就任南洋大學校長,強力推動教育改革,除中華語文科外,全部課程改用英語教學。南洋大學成為一所「副牌的英文大學」,失去了從建校以來頂住重重壓力才保住的特色: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但李光耀還是說:
「在南大理事會一致同意下,我於1975年3月派教育部長李昭銘到南大出任校長。他的任務是嘗試把南大變成雙語大學,但是不成功,因為雲南園的華文氛圍太根深蒂固,師生陷在完全用華文的環境太深,絲毫改變不了。這個任務對李昭銘太過艱難,他只堅持了17個月就離開了。」

1978年3月4日,南大理事會和新大理事會發表聯合聲明,宣布由本學年起兩間大學建立聯合校園,這樣南大學生能夠在講英語環境里學習,從而提高英文水平。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會發表聲明,決定接受李光耀的建議,把新大與南大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1980年4月10日,李光耀致信說:
「我相信讓南大象徵繼續保存下去對我國是有價值的:它敘述了一個熱愛他們語言、文化和傳統的移民故事,這些人來自三輪車夫、的士司機、小販、書記,以及商人、銀行家,響應設立高等教育的號召,捐出他們的錢給南大。這種精神是可貴的。不幸的是,鼓起對中華文化和傳統深感自豪的那些理想,並沒有作為建立畢業生能夠經起市場考驗的大學教育的實際現實。」
南洋大學從歷史上消失了。
再見,雲南園。它並沒有被返還給捐款、捐地的華人以及相關團體,而是把它改造成了南洋理工學院,也就是現在的南洋理工大學。此南洋和彼南洋並沒有一點點關係。今天我們再走進當年的行政大樓,會發現它被改造成了「華裔館」。
再見,相思樹。它曾經長得漫山遍野,在南洋大學關閉之後,它也被「清算」了。
再見,八角亭。當年亭上有特別燒制的、有南大印記的綠瓦。
再見,南大牌坊。當年牌坊上的校名是于右任題寫的,如今南洋理工大學校園中的牌坊,是1995年重建的仿品。
再見,陳六使先生。
我們從南洋大學的關閉中看到了太多的不舍,太多的悲痛。但是在滾滾的時代大潮前,南洋大學不過是一艘小小的船,它在驚濤駭浪中航行了27年,它換了很多任掌舵人,但風浪越來越大,它只能停下——它太累了。
只有那些南洋大學的畢業生們、教職工們、關心南大的新馬華人們,以及從1974年6月15日起就安置在行政大樓里的銅像,他們的聲音還在新加坡的上空迴蕩。

有一位南洋大學的肄業生寫了一篇《My Old Days at Nantah》,此時他已經獲得了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博士學位,他說
「在離開南大的往後數年裡,我經常在夢中回返南大完成我的學業。但是現實卻是殘忍的,因為我的南大母親已經死了。……我身為自已是南大的一名孩子而感到驕傲,雖然我無能成為南大畢業生。」
1981年2月,莫邪寫了一首詩歌《山鬼》:
相思樹已死/相思不死/窮盡碧落無處寫此沉冤/每一顆紅豆都是我/黃泉之下的血淚/而歷史/拒絕記載/城陷之日我攬鏡微笑/雕欄玉砌再也不屬於我/我終身蹁躚為春日群蝶/將一脈風流/植出鏗鏘的千萬花魂遍大地/江山信美兮我何所棲
1984年,著名女詩人淡瑩以詩歌《驚變》描述她參觀南大遺址的感慨,她仿佛又看到了三十年前「草根們」熱火朝天為南大募捐的場景,但過去已成灰燼:
「看!那如拳頭粗的鐵鎖/寒光懾人,森森然/鎖住了文、理、商學院/鎖死了每間課室里的/春風。小草不能再生/所有根須都被刈除,包括/賣冰水、踩三輪的血汗/包括販夫、走卒的感情。」「還有湖光,還有山色/一羅厘一羅厘被載走/日後回來尋覓/應以何處為起點? / /夜的黑爪,霍地張開/我握著軸的兩端/將心情 慢慢捲起/從滿目瘡痍中/一步一回首/走出這幅/這幅青山綠水。」
1987 年 3 月,希尼爾寫下了《曾經》,就在這一年,新加坡全面採用英語作為全國教學媒介語,華校教育走向窮途末路,這首歌中借祖母而透露出的哀傷因此顯得更加真實:
「我說,我已忘了去時路/祖母十分的不悅/敬愛的祖母/為孫不能告訴您真相/曾經,相思千千,那段綠蔭路/已橫斷為二,徒留孤樹一棵/那牌坊,您會因為它不叫做南大而不再愛這湖/歷經風雨,心中的城/幾乎拆塌,幾乎讓您/失去,這一生中/唯一美麗的回憶」
與《曾經》幾乎同時,杜紅寫下了《無名牌坊》:
「四年之間/每天經過牌坊/都懶得望一望/ /誰知三十年後的今天/聽說要拆那牌坊/我卻無限心傷/ /跑了十三哩半/最後一次看看牌坊/不見了題字,不見了一九五五年/ /無限心傷/掏出心中的牌坊/還圍繞著相思樹,還留著當年。」
這些不只是詩歌,它們是血淚,是控訴,是對華人之火將熄的恐懼,是對母語文化消散星城的嘆息。流川在創作於《無法償還的債——重回南大舊址感懷》稱之為「透支了多少鏗鏘傳統,文化上的龐大赤字」。新加坡的華人知識分子遭遇到了嚴重的心理創傷,在新馬華文文學史上,自1980年以來,進入到了「傷痕文學」時期,也有一些研究者稱之為「1981以來的黍離之傷時期文學」。何謂「黍離之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