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的華樂圈子中,有一位音樂工作者是不應被忽略的,那就是楊秀偉。我和秀偉結緣,應該是在80年代初。那時候他的嘉興企業專門出售樂器,我也會到他的樂器店裡購買樂器,雖然並不是很熟絡,但知道他在華樂圈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那時候的嘉興企業,店裡除了售賣樂器,還有許多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唱片、樂譜和音樂資料。除此之外,音樂會訊息、音樂會海報,甚至音樂會入場券,也可以在嘉興買到。我的一本音樂評論集《餘韻》也托他在店裡幫忙售賣。
楊秀偉以及店員——夫人錢鳳鳴和她的妹妹,待人和藹可親。有時也看到一些學生或樂手在店裡談天,嘉興成為音樂愛好者喜歡聚集的地方。錢鳳鳴是一位音色優美、有實力的女高音。80年代還曾為新加坡作曲家協會錄製的「新加坡歌曲創作集」(卡式錄音帶)演唱我創作的一首歌《不知道為了什麼》。
多才多藝自通不同樂器
楊秀偉出生於1954年。他於1967年中學時代就參加學校銅樂隊,學習打擊樂。後來應樂團的需要,又學習了許多不同的樂器。華樂方面,他深受哥哥楊秀欽的影響。楊秀欽是琵琶演奏家,也是吳奕明父親吳膺贊(又名吳繼宜)的學生,學習潮州音樂和琵琶。
和許多在那個年代成長的人一樣,當時在新加坡很難找到老師,秀偉演奏的華樂器如笛子、嗩吶、低音提琴、打擊樂,甚至作曲和編曲都靠自學。天資聰穎的他很多樂器都是一學就會。中學時代,他加入了教育部屬下的青年華樂團,團員是各個中學裡篩選出來的華樂精英,演奏水平極高。後來許多團員成了華樂界中的佼佼者和領軍人物。
1968年秀偉加入國家劇場藝術團屬下華樂團,擔任打擊樂手。這個樂團聚集了當時新加坡的華樂好手,成為本地第一個半職業樂團,指揮是來自中國的鄭思森。1971年國家劇場藝術團屬下華樂團解散後,秀偉跟隨當時的指揮李雪玲以及一部分青年華樂團的成員加入人民協會華樂團。當時我也是人民協會華樂團的團員,後來退出了,與友人組織了掘新民族管弦樂團。所以我們之間可說是擦肩而過,並沒有太多的交集。
那時秀偉剛好在國民服役期間,所以加入了後備軍人協會華樂團。當時的指揮是顏民春,主管是陳景文,秀偉在樂隊裡面擔任打擊樂手,也當了6個月的助理主管。後來指揮換成了小提琴家林哲源。
在林哲源執掌後備軍人協會華樂團的時候,曾經辦過幾場比較大型的演出,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4年的《五月協奏》。林哲源本身是小提琴和長笛演奏家,在念中正中學時玩過華樂、指揮過學校華樂團。他在華樂中加進了許多西樂,為本地中西樂混合演奏掀開了新的一幕。那時秀偉正跟女友錢鳳鳴談戀愛,同時期也有不少人拜倒在鳳鳴的石榴裙下。林哲源有意撮合他們,特別製造機會讓他去指揮一組節目。於是他編了三首歌:《茶山新歌》《小曲好唱口難開》《人說山西好風光》給女高音錢鳳鳴演唱,並指揮樂團替她伴奏,演出極為成功。後來秀偉終迎得美人歸。
1971年,新加坡教育部青年華樂團和青年交響樂團一起到瑞士參加國際青年管弦樂大會,秀偉是當時的團員。1972年他帶了青年華樂團的一個華樂小組,當時團員們稱他們為「三楊過周」——楊票敬(笛子)、楊培賢(三弦)、楊秀偉(嗩吶、打擊)與周經豪(二胡),去參加國際地方音樂比賽,獲第二名。

▲青年時期的楊秀偉(左)和楊票敬在教育部課外活動中心排練室
1974年新加坡人民協會成立華樂團,邀請來自香港的吳大江當指揮,吸引了許多新加坡樂手加入並開了好幾場音樂會。例如在國家劇場舉行的大型華樂交響詩《我的祖國》,聽眾反應熱烈,人協華樂團的規模也逐漸壯大,成為在中國以外第一個令人矚目的職業華樂團。
跨香江到神州牽線搭橋

▲楊秀偉與青年華樂團舊團員合影
1976年吳大江把人協華樂團帶到香港演出,轟動了香江。香港於1977年成立了香港中樂團。吳大江受邀回香港,被聘為音樂總監兼指揮。吳大江也邀請了當時在人協華樂團的一些團員去香港,成為基本的專業樂手。秀偉是第一批應邀的團員,其他的團員包括易有伍(高胡)、譚錦成(大提琴)、歐鍾慶(笙)、李志群(笙)和許麗芳(三弦)。錢鳳鳴也跟著楊秀偉到香港,在香港中樂團兼任打擊樂手。第二批過去的有朱文昌(笛子)和楊培賢(三弦)。
在香港中樂團任職期間,秀偉經常進入中國,幫新加坡的音樂家買樂器、向中國音樂家取樂譜等。當時新加坡與中國尚未建立邦交,由於兩國的意識形態不同,所以內政部查得非常嚴,從香港寄到新加坡的文件都經常被檢查,有些樂譜也被扣留和沒收。秀偉只好把樂譜拆開分成幾部分,以郵件的方式寄來新加坡。當時新加坡從事樂曲創作的人極少,所以這些樂譜對樂隊的人幫助很大,對華樂的發展也起了重大的影響。
秀偉在香港中樂團擔任了5年的專業樂手。他除了香港以外,也經常隨團到其他國家演出,但最終倦鳥知還,1981年楊秀偉和錢鳳鳴回到新加坡。
1979年由新加坡人民協會華樂團的演奏家周經豪、楊票敬、沈文友等成立了嘉興企業公司,專門售賣樂器。但因為他們是專業的演奏家,沒有時間看店。楊秀偉回國之後,他們就請他接手樂器店的業務,嘉興企業交由他來掌管。嘉興最初的地址在黃金大廈,後來遷到書城(百勝樓)。我去過多次,每次都看到很多音樂愛好者在選購樂器或聽音樂、購唱片。他的店不只售賣樂器,也是本地樂手互相交流、互通迅息的地方,同時還幫忙一些樂手找到所想要的樂譜和比較特別的樂器。

▲1978年香港中樂團第一屆工會理事舊照(右起第三位為楊秀偉)
嘉興企業主要的業務是售賣華樂器,所以秀偉經常需要到中國辦貨,出席許多貨物交流會或大型展覽會。在中國他認識了許多樂器廠的老闆,都能選到比較好的樂器。許多對樂器有較高要求的樂手都會向他訂購。早年笙和加鍵嗩吶在本地很少有人售賣,是由他首先引進本地的。
秀偉也因此結識了許多中國著名的音樂家,例如北京的劉文金、彭修文、秦鵬章、朴東升,上海的顧冠仁、閔惠芬、瞿春泉、夏飛雲等當代名家。在中國從事華樂的人,沒有人不認識他。許多人都通過他跟中國音樂家聯繫,或到樂器廠選購中意的樂器。有想到中國音樂學院進修的音樂愛好者,秀偉也會盡力幫忙牽線。這無形中使他成為新中兩國音樂家交流的重要渠道。可惜近年來樂器店競爭激烈,嘉興幾年前因虧損過大而停業。不過嘉興企業這個名字,在從事華樂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指導、指揮、演奏及教學的豐富經歷
上世紀80年代秀偉開始到學校組織樂團、教導學生學華樂。1981年他受邀加入新加坡廣播局華樂團任副指揮,同時也是樂團的指導員,指導嗩吶組、低音提琴組,直到88年離開為止。
1982年,我受邀在新加坡國家劇場信託局華族舞蹈團成立一支中西混合樂團。樂團以華樂為主,加入一組西樂如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等。需要時也加入西洋吹管樂器。這支樂隊除了為舞蹈團伴奏以外,每年也有自己的音樂會《東方樂韻》系列。樂團慢慢擴大到70多人以後,就需要多一位指揮來幫忙排練。當時我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楊秀偉,所以邀請他來擔任副指揮。1992年我為了培育年幼的孩子,辭去了樂團指揮之職,樂團就交託給秀偉了。
80年代秀偉又協助馬來西亞吉隆坡的華樂愛好者成立一支樂團——專藝華樂團。當時馬來西亞的華樂人才比較少,專藝華樂團成立以後,他和沈文友、周經豪三人每個星期天輪流飛往吉隆坡指揮、指導這個樂團,直到後來他們能夠獨立。專藝可以說是馬來西亞的第一個專業華樂團。他們也同時主辦了系列的音樂會《風雷引》,這對後來馬來西亞華樂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秀偉說,記得有一次他們搞了一個音樂會《帝王篇》,演奏的都是跟古代宮廷有關的樂曲,例如《長城隨想曲》《月兒高》等。新加坡的客卿演奏家有嗩吶、管子演奏家孟傑和二胡演奏家趙麗,在皇宮劇院演出,為當時的汶川地震籌款。
楊秀偉這一生中台上台下看過、也演過數不清的演出,讓他最難忘的事是:70年代,有一次音樂會要演奏一首中國樂曲《英雄們戰勝了大渡河》,由顏民春指揮,林明釗(Mohamud)吹小嗩吶,他吹大嗩吶。早年新加坡所有演出的曲目都需上呈內政部批准,這首曲有點敏感,演出在即,准證卻遲遲未發。直到演出的前一天,他們只好去找時任部長潘峇厘幫忙,才被批准演出。可說是有驚無險,卻也讓人捏了一把冷汗。

▲2007年10月,新加坡華樂協會秘書長楊秀偉(左)、新加坡華樂團董事朱添壽(右)出席香港中樂團建團三十周年音樂會及第四屆中樂國際研討會——「傳承與流變」,與香港中樂團音樂總監閻惠昌(中)合影
他還記得有一次的演奏會在演奏關迺忠編曲的《變體新水令》,原作曲者是劉天華,由吳大江指揮,奏到某一個地方時樂隊聲部節奏大亂,情況相當危急。他當時擔任大嗩吶演奏,臨危不亂、隨機應變地跟著節奏吹出了旋律,整個樂隊也跟著他的節奏,在指揮的引導下,安然過渡到正常的節奏。
現在新加坡的華樂團中有很多嗩吶手,演奏嗩吶已經很平常、普遍。由於嗩吶的構造比較原始,沒有好的哨子很難吹准,故早年的新加坡極少人吹嗩吶。楊秀偉算是比較先開始從事嗩吶的研究、吹奏和教學的音樂家。後來他也培養了一批年輕的嗩吶手。早年的華樂團里也很少人能夠演奏低音提琴,楊秀偉也是少數開始從事低音提琴演奏和教學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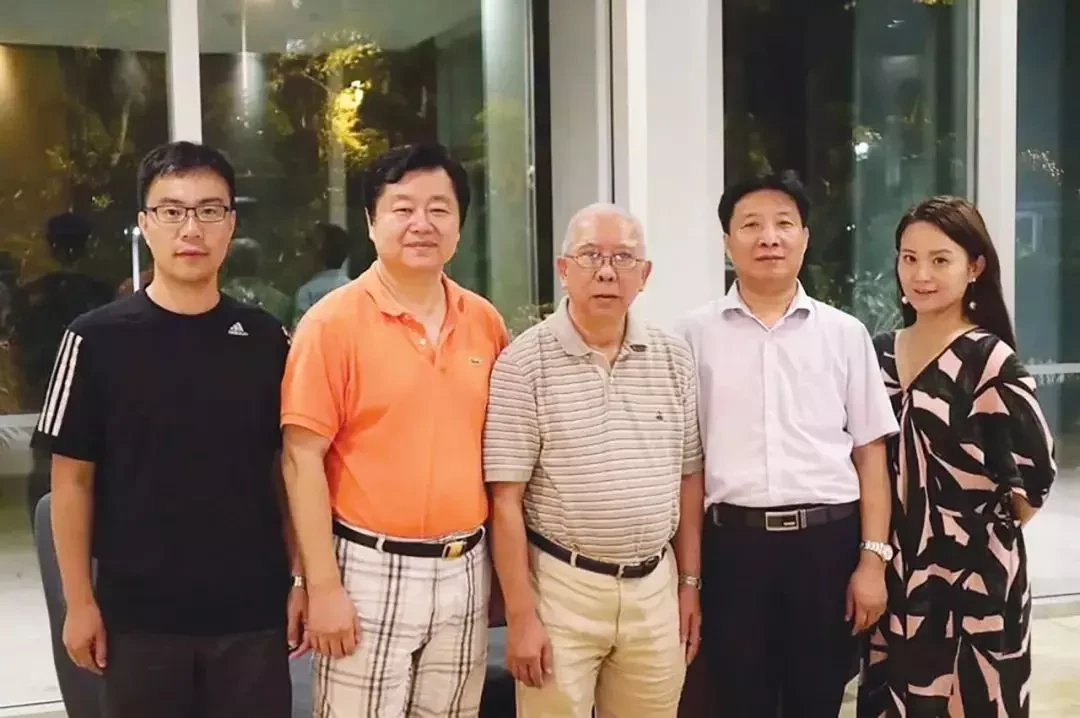
▲與中國的音樂家交流、替國內外的音樂家牽線搭橋,楊秀偉樂此不疲(圖為2017年8月,楊秀偉(中)與中國山東愛樂民族樂團音樂家合影)
穿梭在樂譜上的美妙音符
1992年新加坡成立了華樂協會,楊秀偉被推選為秘書長。2014年新加坡華樂總會成立,他也被推選為秘書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需要像他這樣人脈廣、人緣好的人,才有辦法擔任。
秀偉除了在音樂界是一個很活躍的人物以外,也是一位社區領袖。他幾十年來常在直落布蘭雅區為人民服務,得到政府所頒發的社區服務獎章PBM。他也在新加坡藝術理事會服務了20多年,獲得新加坡新聞通訊及藝術部(MICA)所頒發的SRA獎。
秀偉在華樂界廣聞博識,經常在中、港、台三地走動,看過許多國內外名家演奏,結交了許多音樂家。除了培養、提攜年輕一代的華樂愛好者以外,他的另一個貢獻是替國內外的音樂家牽線搭橋。例如安排中國、台灣和香港等地著名音樂家到我國表演;介紹本地音樂家給外地的音樂團體,讓他們有機會到外地演出;傳遞專業資料、促進學術交流等等。
近年來秀偉飽受病痛的折磨。在訪問的時候,他眉發蒼白、面容疲憊,但一提起有關華樂的事,眉宇間仍難掩喜悅之情。這使我突然想起柳永的詩句:「衣帶漸寬終不悔」。是的,秀偉巧妙而靈活地運用各種人生的機遇,在音樂圈中穿梭忙碌,起初是為了興趣,後來是為了薪火傳承。他熱心幫助和扶持過許許多多的音樂家,雖然並沒有得到太多的物質利益,但他就如樂譜上的美妙音符,帶給人們的是動聽的旋律和內心的富足。
(作者為本地詩人兼作曲家)
(本文首發於《源》165期,文章版權歸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源》雜誌所有,未經授權請勿轉載使用,歡迎朋友圈分享。欲閱讀更多《源》雜誌文章,請掃描以下二維碼,註冊成為《源》雜誌會員,即可閱讀更多精彩文章。為感謝讀者支持,即日起只要註冊帳號,便可享有一年的免費電子版雜誌訂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