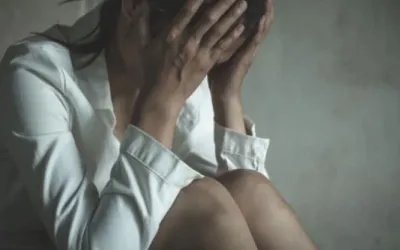小時候的余欣莉、余欣莉(淺藍色上衣)和家人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余欣莉在小學時因為被同學欺負而害怕與他人接觸,連到食堂買東西也成一大考驗。到了少年時期,她發現自己在同學面前和人多的場合時會不停發抖,還會迴避上學,在18歲時被診斷患有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余欣莉的父親對心理健康意識不高,希望幫助女兒的他一度花上千元帶她看中醫,以為這能治好她的「病」。
27歲的余欣莉接受《8視界新聞網》訪問時透露,她在小學時期經常因為各種原因被老師挑出來指責,因此同學們也開始排擠她,給她取名字。漸漸地,她開始害怕與他人接觸。
「以前的老師不像現在的老師一樣。我的老師會因為同學們問太多問題而給與體罰,例如捏學生、扭手臂、拉頭髮、還罰我們站在全班前面。有一次老師嫌我的劉海太長而罵我。我還記得小三那年,每個班級都必須排成兩排,但沒有人願意站在我旁邊。」
到了中三,她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和別人接觸時會感到非常焦慮。老師每周會安排全班學生進行「圓圈時間」(circle time),讓他們排成一個圓圈進行團體活動或發表意見。每當進行活動時,余欣莉就發現自己無法直視同學們的眼睛,雙手和全身開始顫抖,她也為此迴避上學。
到了上工藝教育學院的時候,余欣莉的症狀變得更嚴重,她開始迴避外出,連和自己家人接觸時都會感到緊張,甚至會想作嘔,認為自己受到審視。她為此認為自己一無是處,甚至有輕生的念頭。
她意識到自己必須尋求援助,並在綜合診療所的轉介下到心裡醫生看診,在18歲時被診斷患有社交焦慮症。
社交焦慮症和一般的害羞內向性格有什麼不同?
心理衛生學院情緒管理及焦慮障礙精神科部門精神科副顧問林俊豪醫生表示,社交恐懼症患者可能會刻意迴避社交環境,或帶著強烈的恐懼和焦慮來忍受這種場合。他們也會在受到他人審視的社交場合中感到恐懼,例如在和別人開會時、在他人面前表演或發表演講時等場合。
社交恐懼症患者可能有焦慮症的家族史、曾經被欺凌、遇到新環境或在童年時就展示非常害羞的個性。社交恐懼症一般在青少年中期到成年早期開始形成。
針對余欣莉的情況,林俊豪醫生表示,小時候被欺負可能影響她的長期自尊,進而加劇或延續她在社交場合的焦慮。

經過治療後的余欣莉目前症狀已經沒有那麼嚴重。(圖:受訪者提供)
余欣莉表示,她被診斷後所接受的治療包括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例如治療師會帶她到人多的地方,了解她在這種場合會展示什麼症狀,協助她面對和克服恐懼。
其中一項治療是幻想我如果能和小時候的自己對話,我會對她說什麼。我對我小時候的自己說,很抱歉我無法保護小學時期的你被人欺負。現在你已經安全了,已經沒有人欺負你,你可以放心了。
經過治療後的余欣莉目前症狀已經沒有那麼嚴重,她坦言,她幾乎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只是需要在同事面前發表工作報告時,還是會緊張。
希望心理健康的討論可以變得正常化
余欣莉表示,多年前,人們對心理健康的意識不高。當她向父母透露自己的症狀時,父親因為不了解而用不正當的方法試圖「醫治」她,或對她冷嘲熱諷。
「他會覺得我的舉止很奇怪,會問我『和別人接觸或外出有什麼可怕的』,也會對我說一些不好聽的話。但這是因為老一輩的人可能對心理健康問題不太理解,他還是會以自己的方式幫助我,曾花1000多元帶我去看中醫,以為中醫能『治療』我。」

余欣莉(最左邊)和家人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余欣莉認為,很多時候,有心理健康顧慮的人,要的只不過是有人傾聽,而不是提供建議。
「有時候一些人會提供自以為有建設性的建議,例如,『要不然你去睡覺或做運動,可能心情就會好起來』,但是這些建議可能會讓人覺得他的顧慮不受重視。」
如今,身為社工的余欣莉希望通過成為今年「跨越成見,退去標籤」 (Beyond The Label) 運動大使的身份,分享自己的故事,提高國人的意識,讓心理健康的討論變得正常化。
「有心理健康顧慮是很正常的,你不一定要被診斷患有某種心理健康問題,你可以有某種顧慮,儘管談論它,這並不是一件羞恥的事。我也希望鼓勵有顧慮的人尋求專業幫助,或與朋友和家人談論這些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