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利堅大學 (American University) 國際服務學院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的傑出教授 (Distinguished Professor)、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跨國挑戰與治理講座教授 (UNESCO Chair in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Amitav Acharya 教授在2023年9月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種族和種族主義是現代世界秩序形成的驅動力,其在當前國際關係的塑造中仍有顯著影響。

這場演講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LKYSPP) 舉辦,由 LKYSPP 的院長兼李嘉誠經濟學講座教授 (Li Ka Shing Professor in Economics) 柯成興 (Danny Quah) 主持,探討了種族在世界秩序中的作用。
作為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中心 (Centre on Asia and Globalisation) 舉辦的Hong Siew Ching Speaker Series 的一部分,此次演講還討論了國家為實現更大的自決權、主權平等和免受其他國家干預來解決內部社會內部分裂問題的必要性。
歷史中種族與權力的交織脈絡
Acharya 教授指出,儘管帝國主義和奴隸制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但科學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奴隸制的結合是「西方崛起」的獨特副產品。
他說:「種族主義或種族沒有科學基礎,也沒有基因基礎。種族不是一個生物學事實,而是一個社會神話。在國際關係中,它是一個國際社會神話。」
Acharya 教授在分析中引用了他在《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2022年1月)發表的文章,他指出種族主義、奴隸制和帝國主義是當代以歐洲和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發展的關鍵。這一點從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以及西方重要思想家(如約翰·洛克、伊曼努爾·康德和黑格爾)所倡導的種族觀念中都可以看出,這些思想家對當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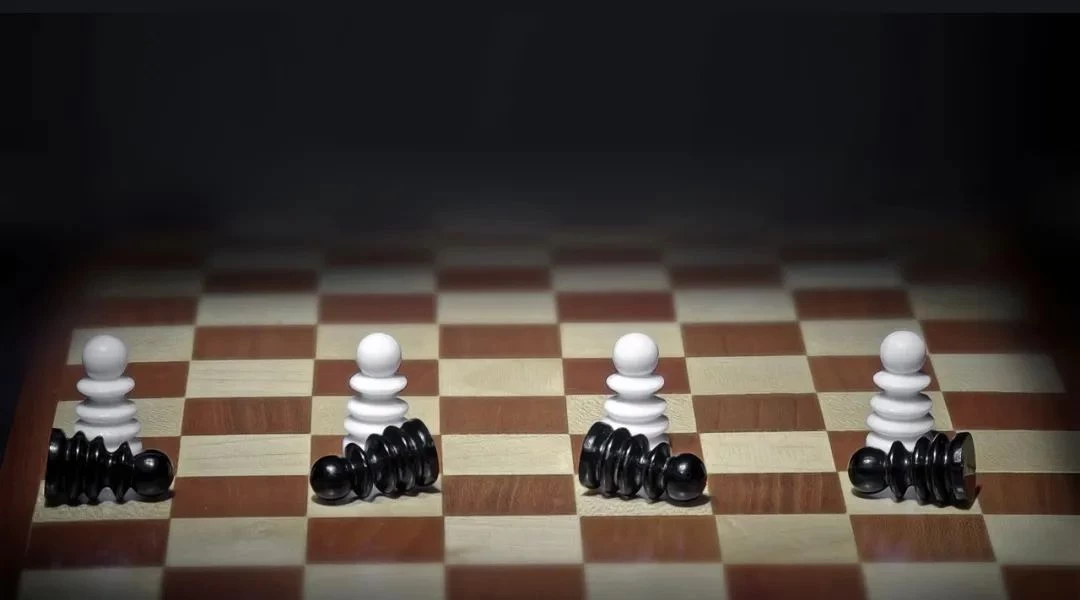
Acharya 教授以康德的教學為例,強調了種族觀念的傳播方式。康德以其倫理學和形上學領域的著作而聞名,但他曾在課堂上傳播種族主義思想。
Acharya 教授指出,這些知名思想家鮮為人知的一面使其成了有爭議的人物,但將他們的作品完全從課程中剔除是不切實際的。相反,他建議在教育大綱中對種族和種族主義問題給予持續性的關注。
萬隆原則 (Bandung Principles) 和
《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
種族主義在「全球化資本主義體系」中得到了合理化和強化,使得西方國家憑藉對眾多殖民地的奴役和剝削而崛起。即便是在去殖民化開始之際,這種權力鬥爭依然存在。
Acharya 教授提到了1955年在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也稱為萬隆會議),並就為何普遍共識認為有必要修改《聯合國憲章》包含對種族歧視的譴責進行了討論,因為萬隆原則的制定就是為了解決這些爭議。他問道:「為什麼萬隆原則本身沒有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和推動力?」

萬隆原則是在萬隆會議上制定的關於譴責種族歧視和殖民主義的十項宣言。
Acharya 教授表示,多年來西方國家對萬隆原則的敵意削弱了其影響力,降低了其可信度。
他回顧了當時西方國家試圖阻止會議舉行並操縱其結果的行為。英國曾試圖說服各國不參加會議,當這不奏效時,便與美國勾結,對與會代表團施加影響,並破壞他們之間的對話。
回到當下,Acharya 教授指出,《聯合國憲章》並沒有特別認可種族不平等問題。他指出,「沒有人可以說他們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中的種族平等原則,(因為)它不在《聯合國憲章》中。」
他說:「導致種族和種族主義在當今國際關係中持續存在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全球種族平等規範。」
學術界的種族主義現象
Acharya 教授展示了幾個圖表,用以追蹤國際關係領域學術寫作中各種術語的使用頻率和流行程度。"主權平等"這一術語在20世紀20年代隨著去殖民化而受到關注,但"種族平等"這一術語卻鮮少被提及。學術界中仍然存在著以傳統主義和嚴格門檻為特徵的種族主義現象。

此外,Acharya 教授還表示,他查閱了舊金山會議 (San Francisco Conference) 的所有22卷記錄,發現其中對「種族主義」或「殖民主義」的提及非常少。實際上,只有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法西斯帝國主義被提及,而法國和英國的帝國主義則被排除在任何討論之外。在《聯合國憲章》中也觀察到了同樣的情況,即使在帝國主義達到頂峰的時期,也很少提到殖民主義。
在引用《聯合國憲章》時,Acharya 教授認為,「人權成為了一個包羅萬象的短語,涵蓋了所有形式的歧視,包括種族歧視……這對那些將種族平等視為獨特規範的人來說是最糟糕的事情。」
國家「內在力量」的關鍵
Acharya 教授提倡各國應以一種「積極主動」的心態來應對種族和種族不平等問題。他引用了自己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雜誌(2022年7月)發表的名為《Hierarchies of Weakness》的文章,該文解釋了與性別、階級、種族、收入不平等和宗教不寬容等相關的「社會裂痕」如何削弱一個國家的力量。

他將這種力量定義為「一個國家管理和減少其國內裂痕、提升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能力」。他認為,這種目標的實現依賴於公民社會的積極參與。通過內部對話和政策解決這些裂痕,國家不僅能夠實現更大的國內穩定,還能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多的力量和影響力。
Quah 教授對此表示贊同,並指出在新加坡,人們清楚地認識到公民社會在維護良好的國內種族關係中的重要性。他以新加坡建屋發展局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的種族融合政策 (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為例。該政策規定了新加坡公共住房中不同種族的比例以「保持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身份,促進種族融合與和諧」。
解決種族不平等和不公正,以及其他社會分裂問題,是釋放國家「內在力量」的關鍵,Acharya 教授認為「內在力量」是決定國家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它也是世界秩序未來的決定因素——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硬實力或軟實力。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3年10月16日,星期一
作者:Global-Is-Asian Staff
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