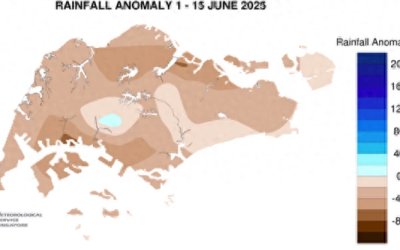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國會以126票贊成、0票反對,同意將新加坡驅逐出聯邦,於是,新加坡共和國正式成立。總理李光耀致力於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座花園城市,一方面種植大量的綠化以穩固沙土,一方面整肅市容以打造東南亞最整潔城市面貌,新加坡的城市化經常被援引為典型的正面事例以供全球其他城市學習。但人類在學習與自然相處的過程仍然是一體兩面的。
基於圖像進行創作的新加坡藝術家趙仁輝,最近發布了兩本全新的藝術家書《新森林》(New Forest)及《新加坡,一顆古老的樹》(Singapore, Very Old Tree,第二版)其實就體現了這兩面。相較於《動植物漫遊指南》,《新森林》和《新加坡,一顆古老的樹》可謂「小」書,不僅在體量上更輕便小巧,內容方面也不需要讀者如猜謎般去揭開科學與攝影術可被人類利用的虛假外衣。

《新森林》

《新加坡,一顆古老的樹》
《新森林》的粉紅色封面,依然會在第一眼給予讀者某些揮之不去的象徵印象:可愛的、活潑的。但這部以牛為主角的視覺歷史,實際上講述的是牛這種動物在新加坡的消亡。和舊時中國許多以牛為重要勞動力的地區一樣,新加坡早年也會馴牛拉車,載人、載水或是載菠蘿。然而,1819年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獲准在新加坡建立貿易站及殖民地之後,代表著工業革命高度成就的小汽車就在這片土地上現身了。隨著汽車速度的提升、效率的增強,取代牛車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另外,在道路行駛仍未得到規範的前現代時期,快速行駛的汽車撞死水牛的事件也逐漸增多。


但導致牛在新加坡徹底消失的主要原因,應該歸咎於新加坡獨立時制定的國家形象——花園城市的目標。牛作為一種「髒兮兮」的品種,與社會進步、城市整潔的訴求相違背,而「新加坡必須呈現東南亞最整潔城市所具備的視覺景觀」。1965年建國之初,新加坡就專門立法驅逐境內所有的牛。結果,曾經在街頭輕易可見的牛就這樣在新加坡的歷史中退場,甚至野外也再也看不到一頭牛。直至2016年,人們在新加坡東北部的科尼島上再次發現了一頭牛,而它或許是新加坡境內最後的一頭牛。遺憾的是,那頭牛也在趙仁輝前去拍攝後的一星期死去。

趙仁輝所攝新加坡的最後一頭牛
全書結合檔案影像以及趙仁輝自己拍攝的照片,還有不同時期各家新聞媒體對牛的記錄,一切包裹在粉紅色封面之中,在輕鬆的音調與不可挽回的悲劇之間得到某種平衡,提供一種更微觀更側面的角度,觀看人類在做出現代化、城市化決策之後對在地共生種群的影響——對應到新加坡的結果是牛徹底消失了,那麼其他城市呢?而對於新加坡,這一最終結果也與政府一向標榜的花園城市、熱愛自然是相左的。


與之相比,《新加坡,一顆古老的樹》可算正面捍衛花園城市的美名,但趙仁輝完全放棄了某種宏大敘事,而將落腳點放在了微觀的個人與樹的關係之上。他採訪了三十位熱愛樹木、植物的普通人,無論是年僅14歲的學生,還是大學研究員、生物學家,甚或簡單稱自己為自然愛好者的人,他們都有在這個城市中最愛的一顆樹。這顆樹或許是早已高齡的原生樹,或許是城市興建後的再生樹,但無論如何,只有當我們看到這些樹木與人真實發生關係了(非砍伐關係而是某種感情聯結),花園城市才有了她最原初以及本應被賦予的意義。

比如有位受訪者二十年前將一顆山竹樹從推土機的巨臂之下救了出來,從此一直守護著它;還有一群佛教徒每天圍繞著一顆橡膠樹打坐冥想,諸如此類。趙仁輝邀請受訪者與他們最愛的樹進行合照,並用手工上色的方式營造懷舊感,雖然與高齡古樹相比,攝影術只能算黃毛小兒,但是用人工的視覺經驗去類比更永恆的樹木的時間,或許可被視作一種嚮往——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可以像這樣的懷舊之感一樣綿延百年,而不成為遺憾的過去,那可以是未來。但採用手工上色或許也僅為對應這個項目誕生的原點:趙仁輝曾在檔案館中見到一張古舊的手工上色明信片,上面標註著「新加坡,一顆古老的樹」。

「新加坡,一顆蒼老的樹」
拍攝於1904年,現存於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趙仁輝的創作一直聚焦於自然與科學、城市發展關係等議題,而這兩組作品都以更微觀、側面的視角去探討他擅長的話題。可以聯繫到假雜誌最近對他的採訪中,他說他遇到的很多科學家或許一生都只研究一種動物,我們可能會覺得一輩子只研究一種動物或許有點無聊,但每個人其實都在努力提供一種自己對自然世界的觀點,這也是趙仁輝在做的事。他也說,人類的認知常常只指向作為人類的自己,以及大自然能為我們提供什麼,但大自然並不為人類而存在,它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存在方式。一旦認識到這一點,觀看世界的方式也會開始轉變。
所有圖片除特別標註 趙仁輝&IC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