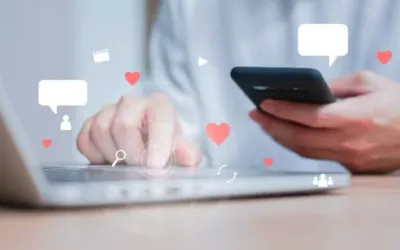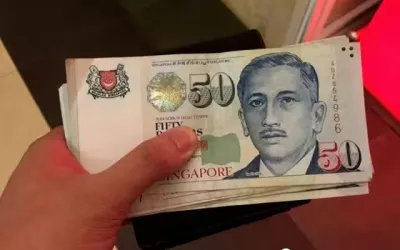轟動新加坡和全球的30億新元洗錢案,總算告一段落。
10名被告已全部被判刑,刑期介於13個月至17個月不等,被充公的資產總值超過9億新元。
值得關注的是,這起新加坡歷來規模最大的洗錢案,也暴露了空殼公司可能淪為犯罪工具的問題。
其中一名被告曾擔任家族理財辦公室(簡稱「家辦」)的董事,但該家辦在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申請稅務津貼時,當局並未在核查過程中發現疑點。
金管局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新加坡約有1400個家辦,遠超過2019年的200個。
越有神秘感 越容易冒充?
家辦是以管理家族資產為主,為家族成員提供各類在地服務為輔的商業機構,可分為單一家辦和聯合家辦。
單一家辦主要集中管理單一家族的財富、投資和傳承規劃。
聯合家辦更像是第三方的財富管理組織,為沒有關聯的多個家族管理財富。

家辦的董事、股東或職員等細節都不容易為外界所知。(聯合早報)
以往提到家辦,大家可能會聯想到億萬富翁,但現在卻更像一個廣泛的標籤。
由於家辦的界定模糊,加上私人財富具有保密性,不論是董事、股東或職員等細節都不容易為外界所知。
正因如此,家辦領域的「冒牌高層」或「蹭流量」現象也愈發猖獗。
業內人士接受彭博社訪問時透露:
假冒者多數是想藉機混入高凈值人士的圈子,以銷售產品或服務;
有的則是靠「高大上」的形象獲取他人信任,方便「賺快錢」,甚至是騙錢。
家辦Oppenheimer Generations Asia董事總經理科萊韋基奧(Edoardo Collevecchio)就曾跟一名假冒者當面打過交道。
他在新加坡的一場商界會議上,碰到一名自稱屬於某個家辦的主講者,於是上前閒聊了幾句,卻發現對方對該家辦一無所知,甚至連家族成員的名字都答不上來。
最後,會議照常舉行,但這名主講者沒有上場。
今年3月,也有一名自稱是「杜拜王子」的男子聲稱有意投資5億美元(約6.76億新元)在香港設立家辦。
後來這項計劃卻無疾而終,更有媒體爆出這名「王子」其實曾以歌手身份在菲律賓出道。

是「杜拜王子」還是「情歌王子」?(南華早報)真富豪刻意低調 假富豪肆無忌憚
許多亞洲地區把家辦視為招商引資的重要對象,但新加坡過去兩年已兩度收緊家辦政策,提高對家辦資產管理規模的門檻。
儘管如此,受訪律師指出,要辨別家辦的真偽,仍存在一些局限和挑戰。
根據康頓研究公司(Campden Research)的調查報告,一個典型的家辦每年的運營成本至少為150萬美元(約203萬新元),意味著流動資產須達到1億美元(約1.35億新元)。
但Dentons瑞德律師事務所營運長劉家銘直言,如果是聯合家辦,實際上可能沒那麼多錢。
「為了給自己『貼金』,方便『混圈子』,一些人會在自我介紹中刻意模糊概念。」
他舉例說,有的家辦幾乎是在一夜之間開設,沒什麼實質內容,服務範圍只是掛名的管理遊艇、買賣房地產或幫富家子弟報名私立學校等等。
反之,一些名正言順的合法家辦卻因擔心「樹大招風」,而刻意模糊自己的身份。
「這些富豪擁有的錢越多,就越不想被登記在冊。」
因此,目前很難根據公開信息來區分真假家辦。

家辦是真是假,要如何辨別?(聯合早報)
為家辦申請者提供諮詢服務的Bayfront Law董事林韋恩建議,最有效且直接的方法,就是查看金管局的投資者警惕名單,了解某個家辦是否被列為欺詐或無照經營。
科萊韋基奧則建議向熟悉家辦領域的消息人士核實,或花時間親自與其他家辦交流。
他透露,以往富二代用來安排社交聚會和打高爾夫球的聊天群組,如今成了用來評估家辦真偽的「情報小組」。
「在WhatsApp上詢問一圈,如果大家都說『不要相信這個人』,那麼消息應該是準確的。」
不活躍就會被除名
加強家辦的監管機制,固然是金管局的工作,但當局更關注的是潛在的洗錢風險。
為應對這個風險,金管局規定獲得稅收優惠的單一家辦,都必須在新加坡銀行開設戶頭。
金管局日前也要求家辦,最遲在這個月底利用新表格提交最新信息,包括聲明:
受益人和員工的國籍和出生地
受益人、董事、代表和股東從未被起訴或定罪
未涉及洗錢活動或恐怖分子融資
所管理的資產未受其他國家的監管影響

金管局出手,便知有沒有。(聯合早報)
金管局也將加大力度撤除「不活躍」的公司。
(「不活躍」指的是連續三年未按照要求向企管局提交年度報告,這些公司通常沒有業務活動。)
企管局的數據顯示:
從2019年至2023年,已有1萬7000家「不活躍」的公司從登記冊上除名。
洗錢案曝光後,金管局對家辦的審查也更加小心翼翼,審批時間從之前的不到六個月,延長到18個月。一些本來有意入駐新加坡的家辦,也因此打退堂鼓。
看來新加坡在爭取家辦投資方面,還是「重質不重量」的。
若來歷不明的非法資金流入新加坡,將損害我國的形象和聲譽;但過度嚴格的監管也可能阻礙合法資金的流入,影響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維持嚴格監管的同時,還要保持對合法資金的開放和包容,這微妙的平衡不容易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