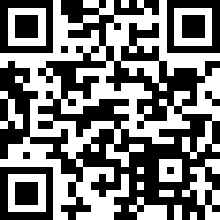2012年,我國總理李顯龍在國慶群眾大會上呼籲,重建更有溫情、更有文化修養的社會,還不忘記提醒國人要更有包容心,寬待外來移民。
翌年5月,他為兀蘭民眾聯絡所主持開幕時,感嘆甘榜精神的消失,並呼籲人民找回舊日的甘榜精神,並協助新移民融入社區生活。
何謂「甘榜精神」?該如何重塑?
「甘榜」是馬來語鄉 (kampung) 的音譯,在50至60年代初的新加坡,居民大多都住在鄉村,鄰里之間守望相助,互相關懷,形成一種和諧、團結的生活氛圍,例如逢年過節,左鄰右舍會一起慶祝;一家有紅白事,其他幾戶也會前來幫忙,大家患難與共,互相扶持,這樣的一種生活氛圍,稱之為甘榜精神。
自1964年我國實施「居者有其屋」政策之後,政府開始興建組屋,把原來生活在甘榜里的每戶每家先後遷移到不同的組屋區。甘榜沒了,隨著日新月異的城市化發展,人們的疏離感與自我保護心態逐漸取代了昔日的鄰里溫情。
這10年來,重建甘榜精神的呼聲不斷,是否就能找回往日那種待人的真情與善意?甘榜情懷是屬於60歲以上那代人的共同記憶,對於年輕的一代來說,可能只是媒體上常見的名詞,沒有體驗過甘榜生活的新移民對它又有什麼看法呢?
張琳
有距離感的存在

張琳(新公民,原籍重慶)21歲來新加坡的一家餐飲店實習,如今是人力資源與移民中介的老闆,她一步一腳印地走來,對社會的人情冷暖頗有感受。她以兩個生活中的例子來說明既近且遠的甘榜精神。
有正義感的社會
總體來說,張琳不覺得新加坡是一個冷漠的社會,她以去年發生在美芝路的一起46歲男子當街持刀追砍前妻的事件為例,指出本地社會還是存有正義感,「事發時,周圍幾家店鋪的員工,還有路人紛紛阻止,使受襲擊的婦女免受進一步的傷害,其實情況是很危險的,但還是有人挺身而出,而不是擔心受累只在一旁圍觀,可見道德與正義感還是普遍存在。」
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都維持一個距離。平時的話,都不會走得太近,如有需要,也有人會站出來,互助精神就是這樣似有還無地隱身於喧鬧的社會中。
「距離,是因為現在的人自我保護意識很強,特別注重個人隱私和空間,這種無形的牆使到社會氛圍跟以前不一樣了。」
甘榜精神有助融入
說到自己的居住環境,張琳認為與鄰里之間的尊重是雙方建立友好關係的基礎。
「像我的前屋主,跟對面的鄰居處得很不好,雙方都裝有攝像頭,互相監視,互相指責,女的說男鄰居一直在偷看她,男的說女鄰居腦筋有問題,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但互不讓步,吵了很多次,最後鬧到警察上門。」
張琳認為,人不是一個個體的存在,鄰里是屬於居住環境的一部分,如果經常投訴、吵架,像戰場一樣,自己也會住得不舒服。她表示,與鄰居的關係應該順其自然,不需要太刻意,如果雙方有共同的話題,不妨多聊幾句;如果沒有,至少也要維持一定的尊重。
「政府一直呼籲居民發揮甘榜精神,目的是為國人製造一個更融洽的生活環境,特別是當越來越多人移民新加坡,鄰里和睦對新移民的融入是有一定的幫助,也可加強新移民的歸屬感,我也希望生活在一個充滿包容、互助精神的社區。」

▲換上娘惹裝的張琳自有一番新體驗。
陳素雯
一切從教育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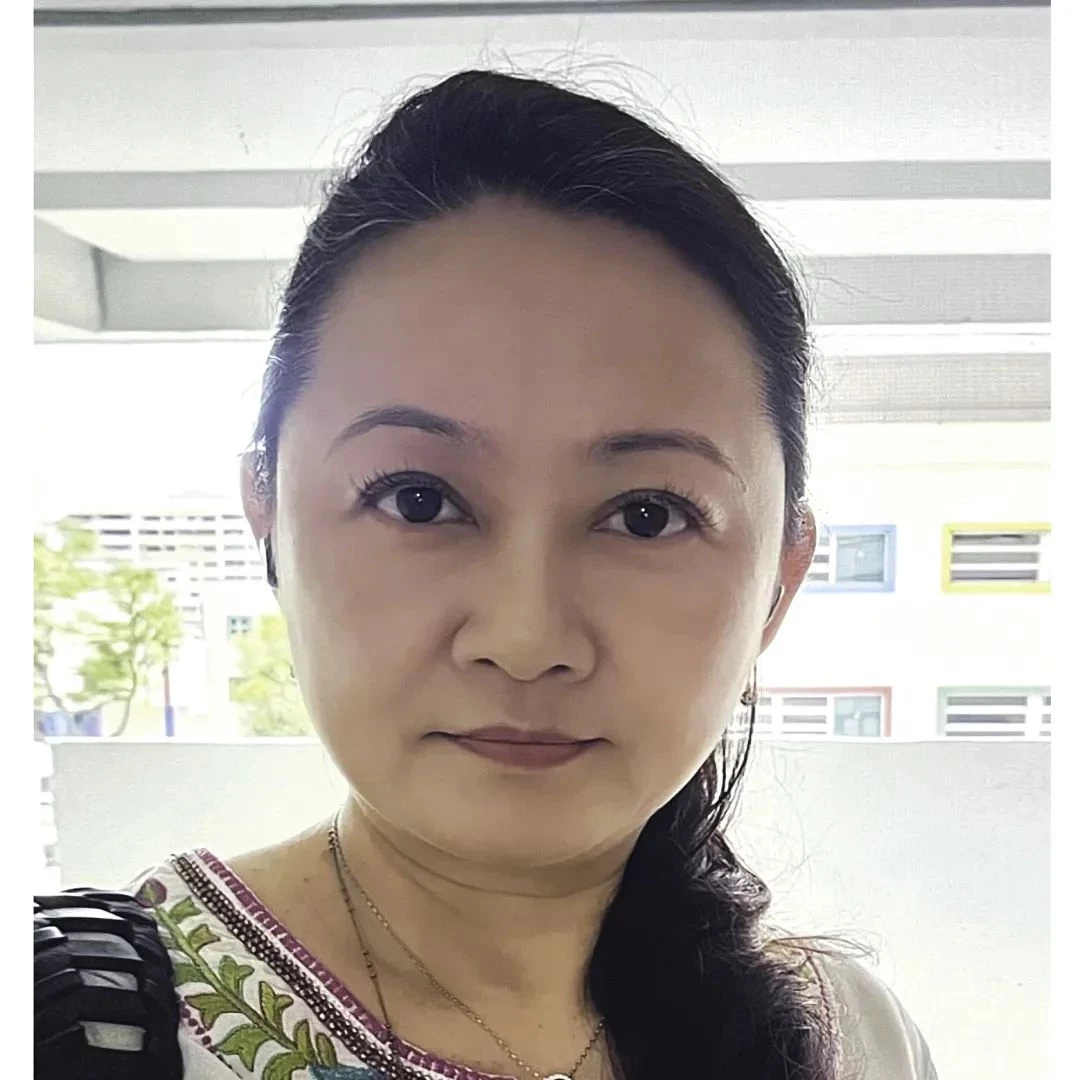
大學行政助理經理陳素雯(永久居民,原籍柔佛)是從甘榜時代走過來的人,在她的記憶中,家裡的大門永遠開著,鄰居做粿沒有麵粉,就跑過來借;電視機開著,左鄰右舍會跑過來看。她說,以前在鄉村環境下交流頻繁,互助關懷發自內心,不像現在。
一切源自教育
陳素雯認為,甘榜精神被社會遺忘,是因為教育的失衡。
「一直以來,學校、家長都只注重功能性的科目,忽略優良傳統價值觀的灌輸,特別是在富裕時代物資充沛下成長的年輕人,在他們眼裡,父母的錢得來容易,根本不知道何謂血汗錢,不懂得體恤、也不懂得感恩。」
因為弟媳過世,她近日經常到弟弟家裡幫忙照顧一對侄女,孩子們的錙銖必較讓她感觸良多,「我叫她們做家務,也需要嘮叨好幾回。她們不但不懂分擔,而且還十分計較,今天你洗碗,明天我掃地,一分一厘也要算清楚,對家人都這麼計較,還能期待她們對社會有付出嗎?更別談什麼甘榜精神。」
她表示,以前的父母還經常攜帶孩子一起做義工,對於孩子或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可在今日已經少見。
有目的性的義工行為
工作之餘,陳素雯還是一名熱心於慈善活動的義工,她參與了各種大小型的義務活動,可這一切對她來說,並不是甘榜精神的再現。

▲陳素雯(前排左二)與義工們周末小聚。
「不要看到很多人做義工,就沾沾自喜地認為是甘榜精神的重現。在我看來,不少義工都是帶有目的性的,早期的義工出錢出力,是令人敬佩的,而現在的義工,有部分是為了獎勵*而做的。例如,做一天義工可獲得20元的禮券,有退休的朋友說,他做義工,一天的伙食費就搞定了,像這種有回報的付出,就不是義工了。」
不過,素雯也指出,在宗鄉會館或宗教團體中還可看到全心全意的付出,就是因為優良的傳統價值觀與道德倫理髮揮了作用。她也一再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否則,培養甘榜精神也只能是紙上談兵。
*有些團體因為需要大量義工,便有一些獎勵制度,例如派發禮物包或獎券等。
大冢龍
存異求同的共同努力

居留新加坡11年,擁有四間髮廊的大冢龍(持創業准證,原籍東京)居住位於丹戎巴葛的共管式公寓,裡面住著許多外籍人士,由於四間髮廊都在附近,他每天騎著腳踏車輪流「巡視」,過著從一個點到另一個點的簡單生活,與本地人的接觸機會不多,可一場防疫讓他走入社區,感受這裡的社會人情。
初次走入社區
2020年因為冠病疫情防控措施,大冢龍的髮廊也被迫暫時停業,他不想終日將自己困在公寓里,便參與疫苗接種的義務工作。與本地人一起工作,對大冢龍來說,是一種嶄新的體驗,也讓他感受到新加坡人對外來者的包容與體貼。
「比較起單一文化的日本人,新加坡人更懂得照顧他人的感受,可能是他們自小在多元文化的環境成長,會很靈敏地感受到對方的情緒,而作出適當的反應,不像在日本社會,對於差異性的容忍度比較差。」
足球隊的合與分
大冢龍一直佩服新加坡政府為加強各族聯繫而作出的積極努力,當他從地鐵與 YouTube 上,看到「重建甘榜精神」的宣傳時,他也理解到政府的用心良苦。
「我參加的足球社就好像一個地球村,會員來自世界各地,大家因為有共同的嗜好,平時都是說說笑笑,不分彼此的,可一旦組隊踢球,就壁壘分明,自然地分為韓國隊、歐洲隊、印度隊、馬來西亞隊、新加坡隊……雖然這樣的分隊,純粹是為了方便隊內的組員溝通,但也顯示出多元本質上的一種脆弱性。」
在關鍵時刻,人會習慣性選擇跟文化相同背景的在一起,這也反映了本地社會的潛在危機。
「培養甘榜精神可讓不同背景的居民,通過日常培養感情,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維繫一個和諧、合作的社區。感情會隨著時間滋長,也可讓居民跨越文化的溝渠,為創建美好生活、共同目標而努力。」

▲大冢龍(前排右一)與足球隊成員合照。
據他觀察,新加坡社會的融合還在「一半一半」的狀態中,「當然我沒有實際的數字,這只是一個方便的說法,我覺得一半的新加坡人已在身體力行中;而另一半,還是保守地活在自己的圈子,他們可能知道但沒有做到,尚在努力中。」
噶孜
像接力一個傳一個

噶孜 (Ghazi Abu Taher) 是來自孟加拉的印族人,2015年入籍為新公民。他是居民委員會(居民聯繫網前身)的要員之一,同時也是馬來活動執行委員會 (Malay Activity Executive Committees) 的執委。62歲的他活躍於社區活動,遊走於不同宗教、種族之間,致力於推廣居民融合,社區聯繫。
環境的重要
噶孜認為,實現甘榜精神,就必須創建一個讓居民可以互動的平台,而聯絡所與居委會正好是「現代甘榜」的中心,通過舉辦各類聯誼活動,將不同語言、種族、教育與文化背景的人召集在同一個平台上,增進互動,加深了解。

▲噶孜(前排右三)與一眾居民、職員攝於正華民眾聯絡所。
「組屋區其實是新加坡社會的縮影,共同生活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如何在保留自己文化根基的同時融入多元社會,一直是國人所面對的挑戰。培養甘榜精神可說是為大家設下了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為自己創建一個和睦、互助的生活環境,也強化了歸屬感與凝聚力。」
把愛傳開去
雖說,甘榜精神的淡薄是不爭的事實,可噶孜認為只要堅持不懈,一切都能水到渠成,事在人為而已。
猶記得初來乍到的他,對社區的一切都很陌生。有一晚,他在公園裡遇見一名快步走的老婦人,大家寒暄了幾句之後,對方邀請他一起走,事後還帶他到居委會,鼓勵他多參加社區活動,種下他日後加入居委會的因緣。
「我很幸運地遇見 Mei Ling(老婦名字),其實她可以完全不理會我,但她還是無條件地協助我這麼一個陌生人。」噶孜強調,以身作則就是最好的教育,畢竟甘榜精神是一種源自內心的自覺,而不是一種機械的動作。
「當一個人感受到別人的好意,他自然也會將這份好意傳遞給另一個人,一個接一個,這種互助的精神自然就傳開去。每個人只是付出一點點,但成效可以很大。」
他說,環境只是創建了利好條件,真正發揮力量的還是來自一個人的自覺。
(圖:iStock、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