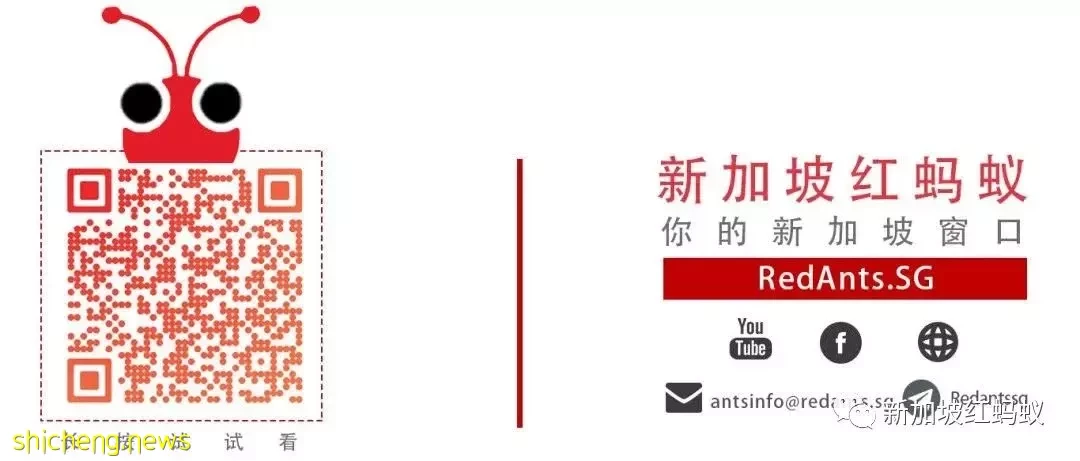我國當局有意扭轉本地過去長時間過度側重腦力工作的趨勢。(聯合早報)
作者 李國豪
下列情境,相信有不少人聽過、遇過,甚或曾經這麼做過:
「家長指著體力工作者向孩子說,『如果你不好好讀書,以後就會和他一樣。』」
這是某些人刺激下一代努力向學的方式,縱使本身沒有惡意,卻也無意間刺痛他人。
但在未來,這必須是本地社會盡力避免上演的場景。
無可否認,考好成績,上好大學,坐在冷氣辦公室用腦力工作,這些本地盛行已久的成功定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新加坡經濟蓬勃發展,邁向先進國之列的基礎。
但時代不同,世界瞬息萬變,過去成功的模式,不盡然持久永恆。新加坡對成功的定義,也到了該做出改變的時候。
這是下一代新加坡領導團隊必須迎接的挑戰。
從周一(17日)的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到前天(18日)的教育部長陳振聲,兩人都在國會針對新加坡未來對成功定義必須做出的改變發表了相關演說。
不再唯有讀書高
黃循財說,本地社會對「唯才是用」的定義太過狹隘,未來新加坡必須跳脫出受限於搶讀名校和過度重視成績的框架。
這包括不再以薪水和資產等物質條件衡量成功,不再學歷至上,致使國人前仆後繼湧向追求學術表現的成功窄門。
相反的,黃循財呼籲國人,應給自己和下一代更多空間,去發掘及發展才能。
這些才能,不僅止於學術,也包括了各種技能,讓每個人都能發揮最大的潛力,成為「最好的自己」。
換句話說,除了腦力工作者,「心件工作」(heart work)和「手藝工作」(hand work)也同等重要。 陳振聲強調,新加坡社會「須要各種角色互補,才能良好運作」。

須掌握技能的工作新的成功定義下,應與腦力工作同等重要。(聯合早報)
不再「一考定終生」
在當今的社會氛圍下,重要考試放榜堪稱是廣大學子的人生大事。
成績優異者,欣喜若狂,仿佛未來生涯已是康莊大道;考差者,難過落淚,似乎前途一片迷茫。
但這種一考定終生的片段,未來將是新加坡新成功定義下必須極力避免的現象。
新加坡未來的「唯才是用」制度,將轉化為「持續的英才制度」(continuous meritocracy),不再以單一時間點的單一表現,決定個人的一生。
黃循財指出,新加坡未來的唯才是用制度必須是持續性的,讓國人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能有學習機會。
陳振聲則指出,若只用單一、僵化和及狹隘的衡量標準,社會容易停滯不前。
「人們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成長步伐,也會展現出不同的能力。」
因此,政府未來將致力於避免用單一準繩,如考試成績或學歷文憑來評估一個人的能力,本地社會及僱主也應避免對國人做出這類「一考定生死」的評斷。
黃循財說,新加坡立志建立一個完善的終身學習社會。
陳振聲則強調,未來我國的教育制度將更靈活,提供多種途徑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政府將持續協助國人在一生中持續學習和訓練,以保持競爭力。
更多國人未來不一定只能在工作前獲取相關文憑證書。相反的,他們在工作之餘,也能透過進修這麼做。
概括來說,便是「行行出狀元」及「活到老學到老」的充分實踐。

在新的成功定義下,個人的人生途徑將不再由單一考試成績左右。(聯合早報)
施比受更有福
無可避免的是,在新的成功定義下,水電工等手藝工作者,以及服務業和社區關懷等心件工作者也必須取得更高的收入回報,以提高國人投入相關行業的意願。
這意味著企業應根據技能和能力,公平地僱傭、培訓和獎勵員工,本地社會也必須願意為某些服務支付更高的費用。
否則,如果特定行業的收入和工作環境並未獲得改善,單靠社會思維和教育制度等面向的改變,恐怕不足以確保新的成功定義奏效。
陳振聲在國會引用華文諺語「施比受更有福」來呼籲國人在新的成功定義下,做出適當的心理調適。
他說,社會必須為改善較弱勢群體的生活做出更多努力,為下一代塑造正確價值觀,讓他們成長為願意為他人創造機會,「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人物。
這包括鼓勵更多來自名校的校友為更廣大的校群做出貢獻,與下一代分享人脈,避免長期的「唯才是用」制度形成封閉的社交網絡,進而造成成功者下一代繼續成功,弱勢者下一代卻繼續弱勢的階級複製情況。
黃循財則表示,新加坡人應該少關注一點「我自己」(I and me),多關注一點「我們大家」(us and we):
「當社會上最弱勢的人也能過上好的生活,所有人都會有所收穫,(因為)我們會成為更好的人,更公平及更平等的社會。」

黃循財(右)與陳振聲(左)先後針對新加坡未來成功的定義發表演說。(紅螞蟻製圖)
要讓長期根深蒂固的成功定義產生如此巨大的改變,國人的思維,僱主的配合,及政策的調整,缺一不可。
但套句陳振聲的話,新加坡故事是「現在進行式」,新加坡人不能自滿,誤以為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可以不做任何改善:
「任何沒有長進的制度終將枯萎。」
期盼有一天,本地不必再上演體力工作者被當成「負面教材」的心碎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