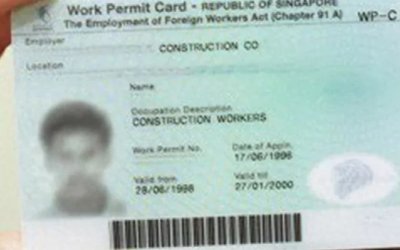「哦,那你知道小鮮肉什麼意思嗎?」
「當然知道!」立園拿著抹布湊過來,搶著回答。「爸爸去哪兒,奔跑吧兄弟,都看過。」
Doris和立園來自馬來西亞,住同一條村,上同一間小學中學。12歲一起去超市打零工,後來一起輟學。立園三年前和姐姐來新加坡打工,Doris也跟著來了。房子租在宜家附近,兩人好的如姐妹。

「你們有男朋友了嗎?」 我問。
「我沒有。」立園自告奮勇。「她有!」 手肘推了推旁邊的Doris。
「哪有嘛!」
「哦,她只是暗戀。」
「誰呀誰呀?宜家的嗎?」
Doris抿著嘴,努力把秘密留在心底。可不聽話的甜蜜,還是撐開一道縫,像熟透了的石榴。
「全世界都知道啦,還故意藏什麼嘛。」力園說,丹鳳眼不停慫恿Doris。
「他嘛……」
「你們幾個在裡面幹嘛?有Customer啦!還不出來!」
聲音從外頭衝進來,像上課鈴,又重又響。
我們三個像被大人訓斥的小孩,偷偷交換了眼神,灰溜溜地四處逃竄。
看我回到崗位,Aunty Angie尖辣的眼珠子瞪過來,再次強調:「別到處亂跑!」我一直懷疑她是獅子座,凡事要稱王。說話又硬邦邦,像個椰子殼,不讓人靠太近。
我埋頭夾熱狗,明知道自己錯了也沒搭理她。過了一會,她來下命令。
「哎,去拿鎖匙,把冰激凌硬幣收回來。」
「鑰匙。」我糾正。
「什麼?」
「標準普通話,鑰匙,不是鎖匙。」
我解釋得很認真,她卻像聽了天大的笑話,咕咕笑起來:
「鑰匙,鑰匙,要死咩!哈哈!」
她笑起來真不好看,也不自然。臉頰兩團很高的肉,因為整天凶著臉,缺乏運動,很僵硬。可是,看她帽子下的寶藍色頭箍,平時拿的粉綠手提包,少女心還鮮活如空氣。這個整天愛叉腰的厲害角色,什麼時候長出來的呢?

「Tong Yan, 你今天負責後勤清潔。」
一上班,就接到任務指示,來自值班經理,一位老uncle。
「……可是……」
「可是什麼?」
「還沒上手啊……」我顯出很難為的樣子。「要不推到下次?」
「沒關係呀,不懂可以來問我。」 他慈眉善目,像極了「功夫熊貓」里那位師傅,讓人不好意思拒絕。「今天人手不足,就拜託你啦。」
說罷,把手往背後一掛,仙人道長般駕著彩雲飄走。
我嘆了一口氣。

後勤清潔,俗稱打雜,功能強大,角色渺小,典型吃力不討好。學經濟的朋友評論,這叫Two-factor theory。大意實例為,熱狗放在番茄醬桶前,壓得出來,沒人在乎裡面裝得滿還是少。要是壓不出來,顧客肯定開始呱呱叫:「哎,醬沒有啦!找人出來滿上!」
這個「人」,現在輪到我。
從台前轉到幕後,有些失落。倒不是因為工作量比以前大多了,喝的咖啡、汽水,用的吸管、紙巾,到顧客拍拍屁股走人後的垃圾,全由我一人來負責。每周兩次消耗卡路里,健身房都免了。
我只是心疼自己的學歷,就像看著新皮鞋踩到泥巴里。名校畢業,出國深造,本該一路向北,卻自由落體,最後怎麼落到連自己都辨不清的路上?
不想被熟人認出,我把帽子壓得很低,遮住大半張臉,只露出嘴巴呼吸。刻意帶上橡膠手套,好與物體隔出點距離。我拿上抹布,穿梭在不同人群與桌子之間。沒有人注意到,這個做清潔的女子,身上裹著厚厚的自尊心。我還把敵人都假想好了,要是誰過來指指點點,說三道四,我一定狠狠罵回去!
「謝謝!」
一把聲音,很真誠。
眼光偷偷從帽檐下越出去,窺見中年女子,帶眼鏡。她好像很過意不去,連忙拿起冷飲與食物,往後退幾步,好給我騰出工作的地兒。
我不太相信,假裝沒聽見,繼續用力擦。
「謝謝!」
是幾個年輕小伙。
我把餐飲區和垃圾桶擦了一圈,耳邊不絕相似的「謝謝」。都說這是一個帶魔法的詞,真的。我猛然覺得自己很可笑,像裹著好幾層大衣,出現在大夏天。碩士打雜,那又咋啦?天跌下來當被蓋!
「謝謝」 我說,順手把帽子高高揚起。
漸漸發現,這份工作也有好玩的,例如倒騰冰激凌機。
別看這鐵皮機器,餓起來也像嬰兒一樣呱呱大叫。只要聽見外面傳來「滴滴滴」聲音,我就得把「食料」,水桶抹布,一樣樣搬上小車,輪子咕嚕咕嚕,緩緩上場。
冰激凌秀開幕啦!
觀眾每人手執雪糕筒,翹首看著我爬上凳子,準備開啟機器嘴巴——一個類似高壓鍋的裝置。我先開到一半,好讓氣體滋遛滋遛釋放一會。全部掀開後,再倒入兩包五公升奶油混合液體。這時,人群總出現騷動,連走過的顧客也要駐足停留,發出感嘆:
「啊,原來冰激凌是這麼來的!」
合上嘴巴,機器像打了飽嗝,渾身顫一下,一切又恢復正常。投入硬幣,放了雪糕筒的鐵圈平穩升起。「噗」,一團雪白雲霧噴出,鐵圈平穩降落。
「啊, 哈哈!」 小孩子激動得又跳又拍手,像遇到會說話的小狗。
「謝謝你!冰激凌機器人!」
表演結束,走回後廚房路上,抬頭看了看鐘:九點半。前後不到岸的時刻,尤其覺得累。 就像馬拉松過了大半,消耗值降至最低點。支撐下去,只剩下意志。
倒了些水,一飲而盡。剛想坐下歇歇,耳邊響起按不下去的鬧鐘:
「Tong Yan,咖啡桶滿了。」
「第一台冰激凌怎麼壞了? 你剛才是不是胡亂操作啦?」

Aunty Angie比值班經理還操心,頻繁從前台崗位退下來,嘮叨我的不是。把咖啡渣倒掉,解釋了機器本來已壞,她還不罷休:
「不是跟你說要一直站在外面,就不聽!看!顧客都來我這裡投訴!」
「投訴」是個很嚴重的詞,她習慣這樣來嚇唬人。很多女孩也因此投降,做乖乖的綿羊。
但我怎麼可能是綿羊?
箭步追上去,昔日叛逆少女現身:
「怎麼做都有意見,你就是在針對我!」
她來不及有反應,我趁勝追擊:
「我媽都管不了,你別想來管我!」
甩頭回到後廚房,該幹嘛幹嘛!
我氣呼呼地跑到餐飲區兜了一圈,抱回一桶快用完的芥末醬。把裝置拆開,放在手龍頭下。手使勁在搓,腦袋卻不停回放剛才那一幕。
」最多一拍兩散,以後井水不犯河水!「 左腦袋憤憤想。可是右腦袋覺得下不了手,有點殘酷。
她不是壞人。
最多就是一張刀子嘴,總惹人煩。可撬開椰子外殼,裡面藏著的心,清甜如果汁。
我是在一次部門派對上發現的。
因為Steven升遷,餐飲部借題發揮,辦了難得的榴槤派對。
那天是傍晚,不知哪兒借來了幾張大圓桌,立在宜家停車場一角。塑料桌布,塑料餐具,大家並不介意。很多人早早來了,吃肉的吃肉,剝皮的剝皮,聊天的聊天,又濃又香的味道,溫暖了鮮有人氣的空間。
待吃空的榴槤殼散落一桌,Aunty Angie才出現。因為不能丟下顧客,聚會吃飯要輪著吃。樓下還有幾個太忙,走不開。
她穿著工作服,剛好坐在我身旁。
「Aunty,你以前是不是黑社會大姐大啊?」 我仗著些酒精,單刀直入。
她一聽,嘿嘿笑起來。「你是說我聲音太大,整天罵人,對不?」
還有自知之明,那到底有沒有?
她沒有馬上回答,而是拿出紙巾,把別人留下的殘羹冷炙,一塊收拾乾淨。三下兩下,面前豁然開朗。
「我呀」,她開始說話,「以前苦命。為了養大孩子,每天打三份工。早上給印度人的服裝店擦窗子,中午飯到珍珠閣(唐人街里的熟食中心)做訂餐,再到酒店做客房清潔。一天睡三小時。現在命好了,孩子拉扯大了。你知道我兒子現在做什麼嗎?」
她自問自答:
「銀行經理!所以我現在出來做工,純屬消遣。要不在家吃著呆著,就真成痴呆啦,哈哈。」
她的笑還是不好看,我卻覺得很可愛。
很快,Aunty要回去上班。臨走時吩咐我幫忙打包些食物和榴槤,她拿下去給他們嘗嘗。
我看著她走上筆直黃線,到盡頭,慢慢消失在電梯里。一回到廚房,她肯定會一邊嘮叨,一邊像喊孩子過來吃飯一樣:」不是餓了嗎? 還不趕緊過來吃!「
Aunty推門進來了。兩隻手一直和脫下來的圍裙慪氣,使勁揉成一團,扔在冰柜上。
「你說不要管你,那以後我一句話也不說!」 她昂頭挺胸,凜然得如女英雄。
我在廚房另一頭,明白了英雄的委屈。
「是為你好!你還這樣對我!」她其實想這樣說。
我放下東西,在圍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她面前:「好啦,Aunty,剛才累嘛。說話就沖點咯。你不要介意啦。」
她怔了一秒,然後,臉上強悍的輪廓,像太陽底下的冰塊,慢慢融化。少女神態,透徹浮現,嬌滴滴的,羞答答的。
她是喜歡被別人哄的,心花都開到窗外了。但又怕別人覺得,快60歲女人了,怎麼還那麼做作,便趕緊拉起皺紋來遮蓋。啞色的秋波,悄悄捎來又悄悄溜走,釀著好幾輩子的情。可以想像,這姿態還原至玫瑰盛開時節,肯定少不了狂蜂浪蝶。
「還不是不想讓你被人罵嘛。」 她努著嘴說。
我伸出手,蹭了蹭她圓渾渾的手臂,表示歉意。她也拿起手,伏在我的上面,拍了拍。她的掌心很硬,很粗,像風乾的牛肉。枯萎了的指甲,暗黃色,冷眼旁觀一場生活劇落幕。

還沒戀上, Doris就失戀了。
我們在等班車。 午夜的新加坡,涼風習習,正好適合聊聊凋謝在花蕾里的愛情故事。
那個男孩是個好人,有求必應,有問必答。自覺不去點破,便是立了貞節牌坊,無可厚非。但電話另一頭的Doris,卻被拋得忽高忽低,想不明白。於是鼓起勇氣,信息里發送心意。
男孩回覆:對不起,我對你沒有感覺。
「去了台灣旅遊,心情好點沒?」我問。
「恩,不太去想了。」
「那時還以為你會做傻事呢!」
「哈哈,不會啦,我還有弟妹要養!」
「會有更好的人出現。 」
「我知道。 謝謝你。 」
她還是那樣笑著,但昏黃路燈下,暈開了淡淡的成熟。
和Doris說了再見,我走向班車。馬來司機剛睡醒,揉揉眼睛,到外面吸菸提神。車上已經坐了幾個人,呼出疲倦的二氧化碳。我跳上車,鑽進深黑的角落。
「Tong yan, 你剛才忘記關冰櫥的燈,我幫你關了。」
Aunty Soo Say邊吃力爬上車邊說,像在播報新聞。
我連聲道歉,很過意不去。
「沒事沒事。」她說,調整了身體與椅子間的契合度。
午夜十二點半,人等齊了,司機扭開馬來語電台,啟動汽車。我閉上眼睛,隨時準備滑入夢鄉。

「今天我做了飯菜才出來做工的。 炒了西蘭花,還弄了個湯。 」
旁邊有人在說話,是 Aunty Soo Say。 我不清楚這是對白還是獨白。但全車就只有我和她同部門,就睜開眼,接過話:
「哦? 給孩子做的?」
「是啊,」 她順得好自然,像早就預感我會在轉角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