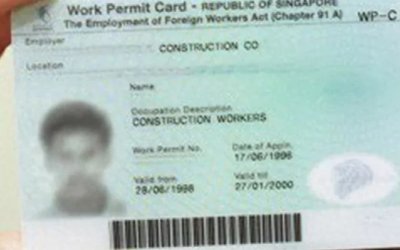「他們上poly (理工學院,介乎中專與大專之間),這幾天準備考試。我先生兩年前走了。 」她說,語氣平淡得有點無奈。
「那你要一個人照顧家庭, 很辛苦啊。」
「我是苦命啦,很小就跟著爸爸出來跑小生意,一輩子沒停過。 現在一個人了,還要供他們讀完書。 」
「Aunty, 你只是勞碌命而已啦。 」
「是是是!你說得對!」她聽上去很感激,仿佛遇到知音。「上次去算命,算命先生也是這麼說。」
然後話題一轉:
「那天去醫院看我媽媽了。」
「沒什麼事吧?」
「老了咯。 過幾天還要去拜拜我爸爸,還有先生。 本想在家裡供佛像, 後來想想算了。 以後我走了, 小孩不懂, 隨便扔掉,不好。 」
電台傳來詭異的音樂,凶宅里的木門,被看不見的東西拂過,幽幽地吱吱作響,女人突然高聲尖叫,把心都喊毛了。低沉的男聲最後冒出來,聽不懂在說什麼,應該是午夜鬼故事節目開場。
車上突然很安靜。 我以為她也被嚇著了,沒想到問題又倔強地站起來:
「你先生疼你嗎?」
「嗯, 挺疼的。」
「那就好。 我先生很顧家的, 一休息就帶孩子出去玩。兩個人結婚,年齡什麼的算啥,會照顧家就好。 」
「哦」。我換了個語氣詞,她沒有留意也不在意,仿佛只要有人回應,就有繼續下去的理由。
「我全身都痛呢。 那天去針灸了,好點。 哎呀, 一次得要好些錢呢。 那天我女兒病了,也去看醫生了,又要花些錢。 」
「你小心身體, 別太累了。 」
「好,謝謝。」
車停了。
Aunty拿出雨傘拐杖,先伸到車外,在地上立穩支撐點,再用另一隻手咬住扶手。身子像一袋大米,在兩點之間,晃了幾下才晃下車。
「謝謝,晚安。」她對大家說。
「晚安。」我說。
門很快合上。
我透過茶色玻璃,看見兩條被嚴重壓彎的腿,一深一淺,一淺一深,艱辛地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