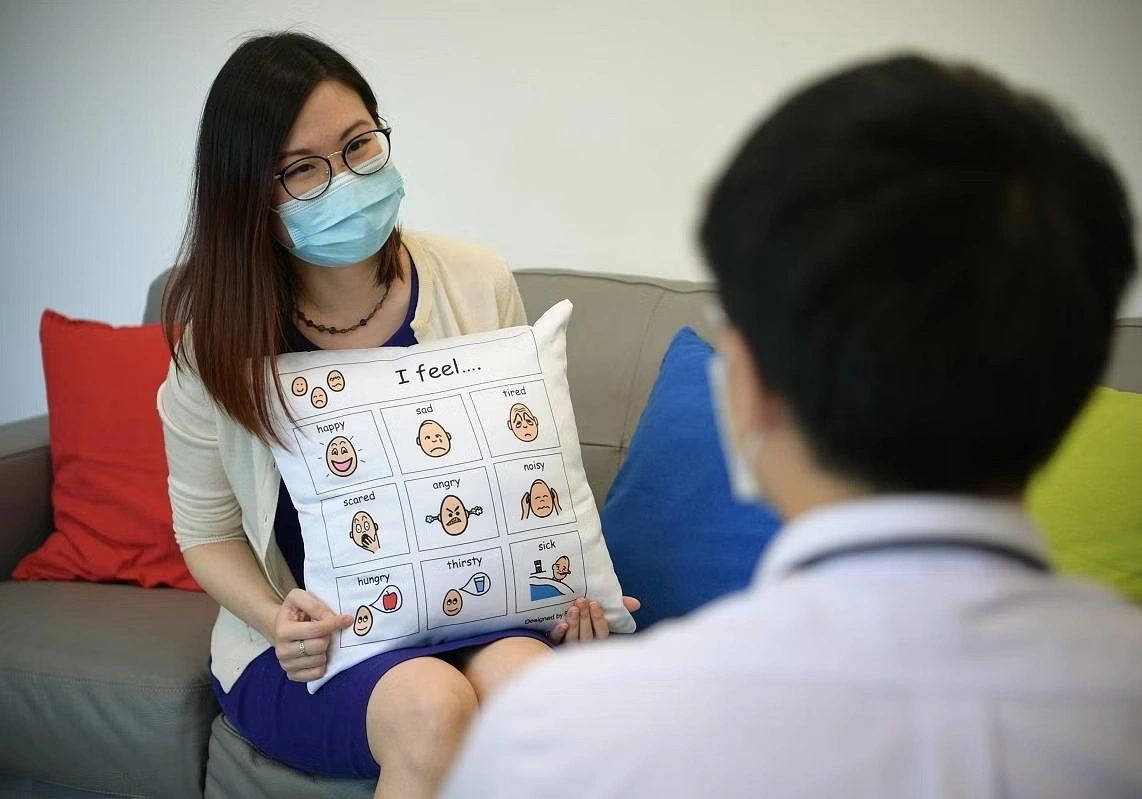
新加坡國會過去幾天針對心理健康動議展開辯論,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尤其受關注。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發言時說,社交媒體和同儕壓力等多方面的影響,導致青少年的整體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青少年一直以來過得不容易,成長過程中少不了焦慮。他們必須了解自己,承擔新的責任,為步入成年做好準備。」
少年十五二十歲時,本就是多愁善感的青春期。
少男少女除了面對生理變化的壓力,也得應付來自課業、同儕和家庭等方面的心理變化,容易產生不安和反叛情緒。畢竟這個年齡層的孩子多數還在求學。

社交媒體是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罪魁禍首」之一。(海峽時報)
據紅螞蟻了解,學校目前的做法是:
當教師觀察到學生出現異常行為或情緒反應,一般會在與家長溝通後,建議駐校輔導員介入。
經過輔導員和師長評估,若認為學生需要專業協助,再轉介到心理衛生學院接受診治。
照理來說,每所學校都會安排一兩名駐校輔導員。偏偏近來駐校輔導員人手不足,解決學生的心理問題竟也成了教師的工作。
我只負責教書?別痴心妄想了
義順集選區議員黃國光(2月7日)在國會為教師們請命,呼籲教育部進一步減少教師的非行政工作。
總理公署部長兼外交部和教育部第二部長孟理齊博士卻如此回應:
「當學生向教師傾訴私人問題時,教師不應該說:『對不起,這不是我的工作,因為我只負責教書。』」
孟理齊強調,教師的工作不僅限於課堂教學,還包括友伴(befriending)和輔導。學生也須掌握生活技能,因此當他們遇到問題或困難時,教師應該陪在身邊給予建議和指導。
「從更廣的層面來看,教師扮演著指引者的角色,陪伴學生走完這趟教育歷程,讓學生了解到教師無時無刻都在。」
孟理齊的這番言論,很快在網上炸開了鍋。
有教師在臉書留言申訴,教師人手越來越少,工作量卻越來越多。
「難怪有那麼多教師產生倦怠,或轉行成為『百萬富翁』補習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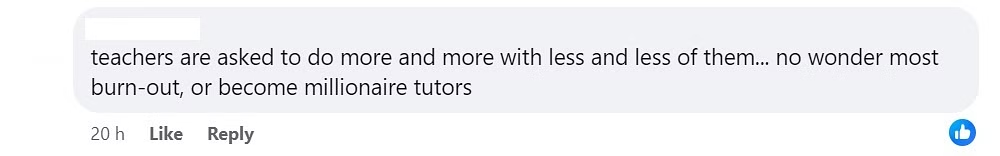
(臉書截圖)
也有教師認為,教師在引導學生方面可以擔任家長的「夥伴」,但不能完全取代家長。
教師每班有三四十名學生要照顧,而家長最多只有三四個孩子要管教。更何況,已婚的教師還有自己的孩子要兼顧。
「關懷青少年的重任必須由家庭承擔。如果把這些責任『外包』,社會對教師的期望未免太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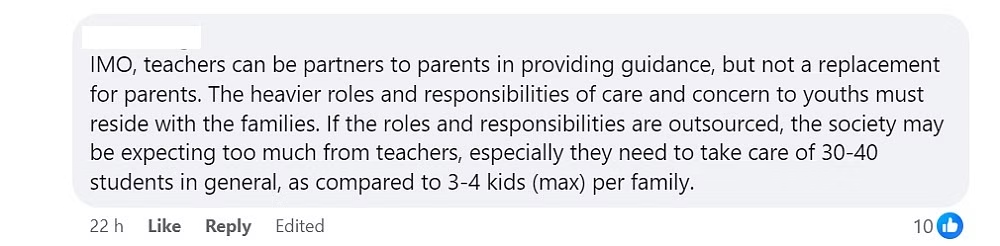
(臉書截圖)教師只有七成時間用在教學相關工作
紅螞蟻沒當過教師,但身邊有不少親友是為人師表。
一名從事教育工作超過10年的親戚開玩笑說,如果教師沒有三頭六臂,根本不可能「包山包海」,身兼數職:
「教師的工作範圍=教師+家長+輔導員+導遊+記者+醫生+活動策劃員+海報設計師+飲食承包商……」
現實生活中,純粹教書的教師並不存在,而想利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教好學生,幾乎可說是痴心妄想。
儘管孟理齊一再強調,教師的工作時長已趨穩,低於之前的平均每周47小時,但一項本地調查顯示:
教師只有七成的工作時間(約33小時)用在與教學相關的工作,例如授課、備課、擬考題和批改作業。
其餘三成時間(約14小時)都花在非教學項目,包括行政事務、課外活動、學習營、帶學生看國民教育演出,以及聯繫家長等。
如今還要教師充當輔導員和「心理健康大使」,實在是強人所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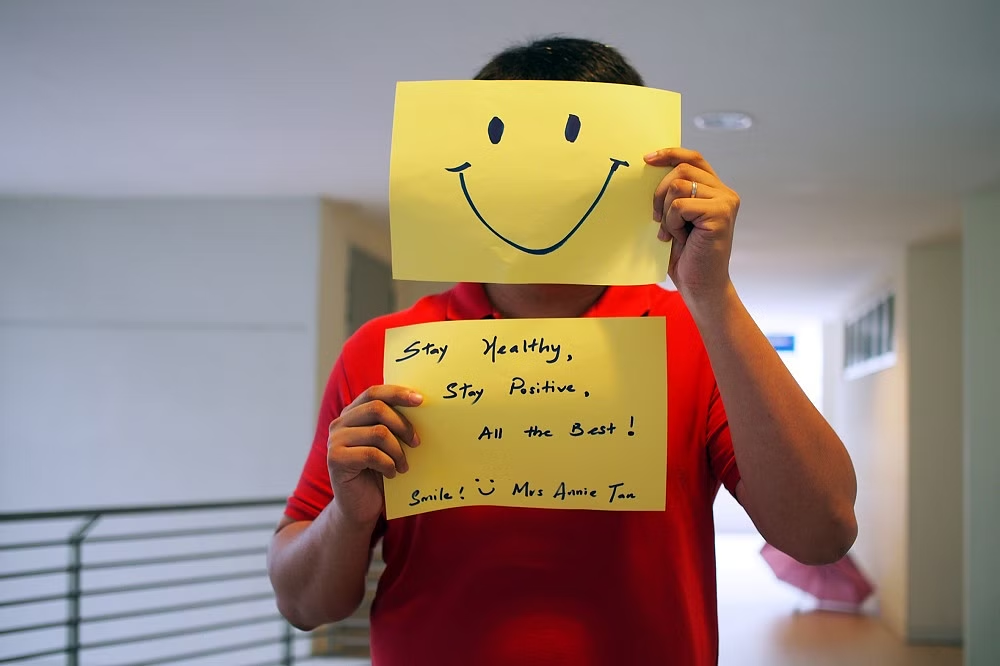
親筆寫下鼓勵字條送給學生,這樣的教師實屬難得。(海峽時報)
教育部長陳振聲曾在2021年宣布,未來幾年將委任1000多名教師輔導員,並提升所有教師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專業培訓,以更有效地輔助有需要的學生。
這些教師輔導員必須接受額外培訓,因此教學工作量會相對減少。
或許是紅螞蟻多慮了:
萬一學生有任何「疑難雜症」都找教師,在情感上對教師過度依賴,產生仰慕之情,甚至發展成師生戀,校方要如何確保教師不會違背職業操守,做出越界行為?
在紅螞蟻看來,幫助學生解決私人問題的「重任」,還是留給家長或駐校輔導員吧。
(雖然很多時候家長本身也可能是孩子的壓力來源……)
或許教育部可以考慮,讓每名學生做例常體檢時「順便」與輔導員面談。這樣就能發現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及時伸出援手。
若真的請不到輔導員,或許可以動員受過心理健康培訓的大學生,定期為中小學生提供輔導。以同輩身份展開對話,或許效果會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