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昱嘉
與抑鬱症默默搏鬥的婦女,有一次在母親入院時與醫護人員產生誤會,頓時崩潰,出手攻擊對方。
法庭認為她的精神狀況影響她犯案,判她接受兩年的強制治療令(Mandatory Treatment Order,簡稱MTO)。她接受治療就不用坐牢,完成療程後也不留案底。
隨著社會更注重心理健康問題,MTO可說配合時代的進展,但有公眾質疑強制治療的效果,甚至懷疑罪犯可能裝病逃脫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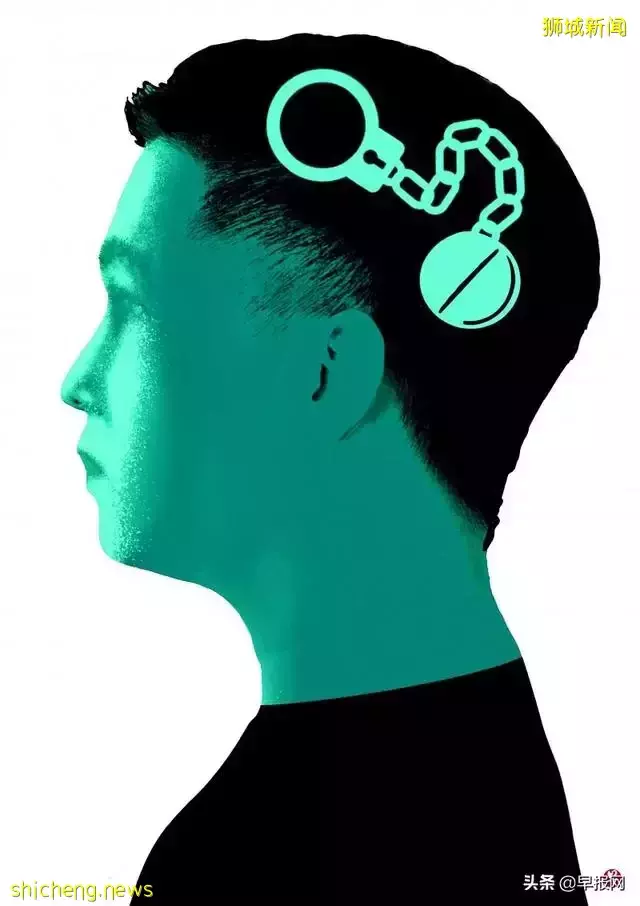
「強制治療令」 是為心理疾病患者開恩還是為罪犯開脫?(梁錦泉製作)
本期《說法識法》邀請心理衛生學院法證精神科高級顧問醫生潘文仔、贏必勝法律事務所的黃國彥律師,
以及Quahe Woo & Palmer律師事務所刑事部門主管蘇呢爾(Sunil Sudheesan)律師,解說強制治療令的作用及效果。
過去10年法庭共發出759個強制治療令,順利完成療程的占約八成,顯示多數罪犯珍惜寶貴的第二次機會。
心理衛生學院提供給《聯合早報》的最新數據顯示,此判刑自2011年實施後至2021年,法庭共發出759個強制治療令,每年平均70個。
法庭決定判強制治療令,並不單憑罪犯自稱患有心理疾病,或私人醫生的意見,而是經過多層鑑定才做出的決定。
心理衛生學院法證精神科高級顧問醫生潘文仔說,罪犯首先要先經過心理衛生學院醫生的評估,看他適不適合接受強制治療,但不是每個人可以在評估階段順利「通關」。
潘文仔醫生也是強制治療令臨床項目醫務總監。他解釋,犯人須符合五大條件:罪犯案發時患有心理疾病、精神狀態顯著影響到犯案、疾病可被治療、罪犯知道他患有心理疾病且願意接受治療,以及罪犯擁有良好的社區扶持。未達到任何一個條件,就可能無法符合MTO的要求,「若評估發現罪犯有傷害他人的風險,也不會被推薦接受MTO。」
評估報告完成後,就提交給控辯雙方和法官過目,最後由法官做出判決。
總檢察署回復《聯合早報》說,通常是在案件的主要判刑考量為改造,且心理疾病顯著影響犯案的情況下,法庭才會判強制治療令;若控方認為此案判刑必須起到阻遏作用,主控官會在庭上提出反對。
但罪犯若沒有代表律師,而控方知道他可能患心理疾病,覺得強制治療令適合此案,也可能會要求法官考慮這個判刑。
MTO通常只涵蓋較輕的罪行,一些罪行完全不可被判MTO。針對哪類罪行不可判強制治療令,律政部發言人回複本報詢問時指出,這包括蓄意重傷他人、非禮、性侵、強姦、謀殺等嚴重罪行。

蓄意重傷他人、非禮、性侵、強姦、謀殺等嚴重罪行不可被判MTO。(示意圖,檔案照)
治療期短為六個月長則三年 必須定時服藥依時看診
強制治療令的療程短則六個月,長則三年。治療期間,罪犯必須定時吃藥、與心理醫生見面,病例護理人員和醫療社工也會督促治療進展。
潘文仔醫生指出,多數罪犯在心理衛生學院接受治療,在其他公共醫院接受治療的例外個案,也得定期讓心理衛生學院的醫生評估病況。
病人必須必須定時服藥依時看診,竇澤案件可能重回法庭審理。(示意圖,檔案照)
若罪犯沒有依時看診、定時服藥或違反強制治療的任何條件,案件可能回到法庭審理,到時法官有權決定對犯人發出警告、更改或延長治療方案,或撤銷強制治療令並重新判刑。
律政部發言人也指出,社區判刑制度於2018年進行改革後,法庭可指定包括強制治療令在內的社區判刑與緩期處刑(suspended sentence,簡稱緩刑)同步進行。若罪犯違反社區判刑的條件,監禁或罰款的判刑將立即生效,這也成了促使罪犯遵守社區服刑的「動力」。
有犯人寧願坐牢也不要接受MTO
別人眼中的寬容對待,有些罪犯卻覺得是「虧待」,他們寧願入獄,也不要進行強制治療。
這是潘文仔醫生觀察的現象。他解釋,有些罪行只附帶短短几周或幾個月的刑期,但強制治療令最長可達36個月,「他們誤以為MTO制約了他們所謂的『自由』。」
他指出,強制治療令實施之前,一律把患有心理疾病的罪犯送入監獄,可能無法有效地對他們的犯罪行為對症下藥。
如今有了MTO,他認為不願接受的罪犯其實目光短淺。「MTO的宗旨在於改造真的患有心理疾病的罪犯,幫他們避免留案底。」
律師建議擴大MTO範圍
受訪律師認為判刑的範圍可以再擴大,更有效地幫助面對心理疾病的罪犯。
蘇呢爾律師認為,強制治療令是非常好的創新點子,但目前還未充分利用。「這是因為控方太常拒絕讓被告進行MTO評估,心理衛生學院也沒有足夠資源擴大MTO的範圍。」
蘇呢爾也指有些罪犯在治療結束後重犯,因此建議延長強制治療期及實行更多措施跟進罪犯進展,以更好地幫助他們。
黃國彥律師也希望強制治療令涵蓋的罪行範圍擴大。他舉例,對公務員使用刑事暴力,或蓄意傷害傭人的罪行都不在MTO範圍內,罪犯就算因心理疾病犯下這些罪行,也無法進行強制治療。
「我們在工作上常見到這些被遺漏的案件,按照法律,這些囚犯都不能獲得MTO。」
裝病矇騙心理醫生?沒那麼容易
有些罪犯視MTO為系統漏洞,認為可裝病擺脫法律責任,但醫生可憑經驗和技能挑出這些人。
潘文仔醫生表示,罪犯是否在裝病,一直以來是評估的首要考量。「負責評估的心理醫生的經驗和技能是關鍵,以挑出裝病且只想『碰碰運氣』的罪犯。」
另外,病例護理人員和醫療社工也會參與評估過程,醫生也可通過心理測驗探測罪犯是否在裝病。若案件比較複雜,醫生也可諮詢上司或同事的意見,潘文仔醫生強調,心理醫生都不必獨自處理案件。
曾負責數起涉及MTO的刑事案,包括引言中提到的抑鬱症婦女案的黃國彥律師也認為,騙過心理衛生學院的醫生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
「(這些醫生)是經過訓練的心理學專家,這是他們每天的工作,犯人的行為若有不一致之處,他們都看得出。」
曾判MTO刑事案件
個案 男醫生偷拍男子
患有適應障礙與偷窺症的新加坡中央醫院前醫生傑里·納加普塔(31歲)2020年面控,指他多次在商場內偷拍男人如廁,心理評估顯示他適合接受強制治療,法官最終判他接受強制治療一年。
個案 大學教授到便利店偷竊
南洋理工大學教授餘明裕(55歲)到便利店偷竊總值400多元財物,他2017年承認偷竊罪時,心理評估顯示他案發時抑鬱發作,法官判他接受18個月強制治療。
個案 婦女騷擾鄰居九年
婦女李吉林(65歲)騷擾馬來鄰居長達九年,包括朝他們丟生豬肉,多次被控蓄意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情感的罪名。她2017年被判接受兩年強制治療,但在治療期結束後繼續騷擾鄰居,2020年再面控時因不肯聽從指示吃藥,不適合再接受強制治療,被判12個月緩刑監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