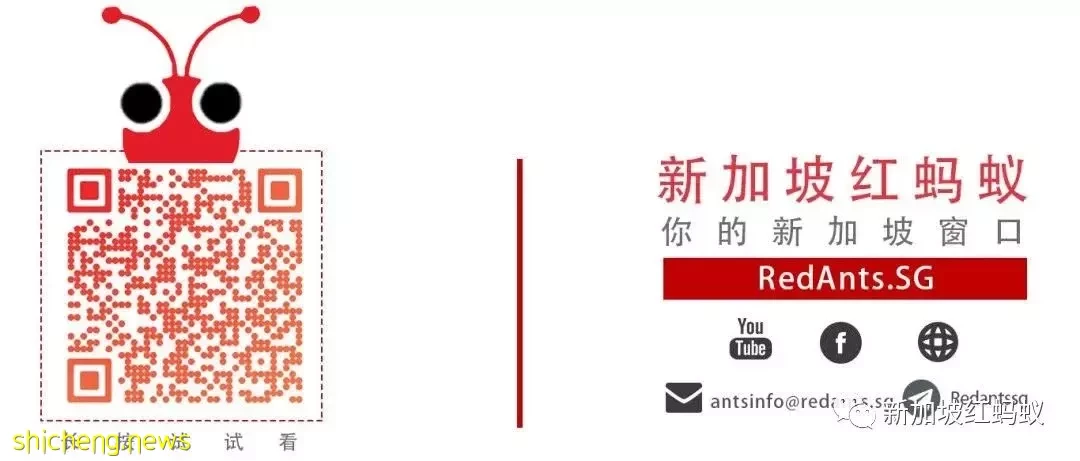研究顯示本地年輕國人中,工藝教育學院畢業生的薪資遠低於大學畢業生。(海峽時報)
作者 李國豪
一項研究指出,21歲至38歲國人當中,有大學文憑或更高學歷者的薪資,足足比工藝教育學院以及中學或更低學歷者多了一倍有餘。
這項由國大國立大學社會服務研究中心進行的研究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期間,共訪問了1905名自年齡介於21歲至38歲的公民。
研究中幾個值得注意的數據:
大學文憑或以上者的月薪中位數為4200新元;
持專業文憑或A水準證書者的月薪中位數為2600新元;
工教院、中學或更低學歷者為2000新元。
大學文憑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數比持有專業文憑或A水準證書者多了62%。
大學文憑或以上者的月入中位數更是工教院、中學或更低學歷者的兩倍有餘。
差距可謂不小,領導這項研究的國大社工系副教授吳瑜虹因此做了一個簡短的總結:
「新加坡非常重視一紙文憑。」
本地三成多人口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
然而,根據2020年最新人口普查,我國25歲以上居民當中,33%為持有大學文憑或更高學歷者。
換言之,至少六成國人的學歷是在大學以下。
2017年,時任教育部長王乙康曾透露,由於我國教育體系必須與經濟結構一致,因此每個年齡段的大學畢業生比例最好能控制在30至40%左右,其餘者則參與各行各業的技職訓練。
從經濟結構健全角度來看,這無可厚非,一個發達經濟體應當理論與實踐並行。
正因如此,在預期本地大學畢業生占人口比例不會超過四成門檻後,較低學歷者與大學學歷者的收入差距如何縮小,已成為極為重要的社會經濟課題。
政策層面,扶助低薪員工的漸進式薪金模式,以及當局推行的各項技能提升計劃,如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SkillsFuture Credit)以及「新心相連」(SGUnited)技能提升計劃等,都是試圖拉近收入差距的努力。
但社會的觀念,是接下來必須因應的挑戰。

本地藍領工作者和白領工作者的收入差距不小。(海峽時報)
近年來,政府和學界顯然已意識到本地社會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氣,是收入不均問題的原因之一。
王乙康2017年曾說,新加坡下來五年面對的最大教育挑戰,是要改變「死死一定要上大學」的心態。
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今年10月也曾表示,工教院與理工學院和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差距令人擔憂,且薪資差距還在他們的一生中持續擴大,是因為新加坡仍過度看重認知能力,即被視為靠腦力的工作(head work)。
他說,在本地,從事其他形式工作的人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例如需要手藝(hands-on work)的技術工作,或需要心件工作(heart work)的服務業和社區關懷職務。
「我們應該尊重那些用雙手、用心勞動的人們,給予他們和其他發展道路者一樣的地位。」

黃循財對大學畢業生和其他學歷者的收入差距表示擔憂。(通訊及新聞部)
金融管理局局長孟文能去年7月也曾在新加坡政策研究所的一場講座中觸及這項課題。
他指出,和其他國家相比,本地許多技術藍領工作的工資相對低於全國薪資中位數,是造成國人收入不均的原因。
例如在新加坡,木匠和電工的收入僅是全國收入中位數的50至55%,相較之下,澳洲、美國和英國則是100%甚至更高。
「在新加坡,這些工作的待遇並不好,也不被視為是有前景的行業。體力活在社會上被污名化,而且常依靠低薪外籍員工去從事這些行業。」
孟文能更建議我國應棄用PMET(專業人士、經理、執行人員和技師)這組詞彙,或至少將開頭的P(專業人士)給去除,因為這個P暗示著技術活並不屬於專業。
他也強調,世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擁有不同技術的分流,以及各種通往成功的道路,因此大部分新加坡人都以成為PMET作為目標的觀念是應該受到質疑的。

孟文能質疑大部分新加坡人都想成為PMET的觀念是否適切。(聯合早報)
從上述幾位政府高官的發言來看,基本上可以理解為,除了採取相關政策,改變社會思維,也是拉近收入差距的必經之路,而且是「人人有責」。
其中最難的恐怕是這一道靈魂拷問:
如果要提高技術工作者的薪資,你是否願意為此付出更多(錢)?
對藍領職業者的重視,除了對其社會地位的尊重,還必須包含國人作為消費者,是否願意為服務及產品付出更高的價格,從實際面認受技職人員的工作及貢獻。
誠如黃循財針對此課題所言: 「我們所有人也必須做好我們的本分,願意為來自各行各業工友們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付出更高的價格。」
以製造水平聞名於世的德國為例,該國技術工作者的薪資水平之所以能與所謂的腦力工作者平起平坐,除了完善的技職教育體系,社會上對技術工作者的敬重亦是。
在日本,在特定領域擁有技術的熟練工匠則被稱為「職人」,他們可以是石工、木工、雕刻師或是料理師傅等,社會地位極其崇高,職人也以自己的工作引以為豪。

德國以其完善技職體系和一絲不苟的製造水平聞名於世。(德國之聲)
無論德國的「匠人」或日本的「職人」精神,皆不是依靠一紙大學文憑在社會上立足。
在精神層面,技術工作讓他們有成就感,在社會上享有尊嚴,現實面,也有不錯的收入過上和「白領」工作者一樣的中產階級生活。
這在大學畢業生薪資水平依舊遠遠拋離其他較低學歷者的新加坡,短時間內難以想像。
假以時日,新加坡社會若能逐漸摒棄文憑至上主義,社會能真正同等珍視技術工作和學術成就的價值,甚至跨過最難的那道坎,國人願意為產品服務付出更高價格,以犒賞技術工作者的貢獻,相信非大學畢業生與大學文憑及更高學歷者之間的收入差距,自然有望進一步拉近,甚至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