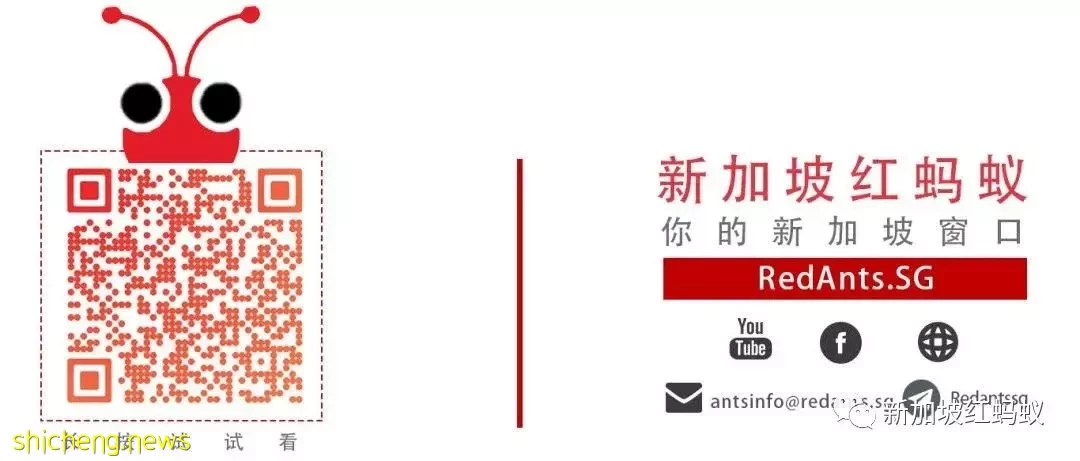讀者投函《海峽時報》,探討如何避免醫護人員和病患之間「雞同鴨講」的狀況出現。(海峽時報檔案照片)
作者 王震宇
紅螞蟻依稀記得,童年時有這麼一幕:
外婆身體出現了疑似糖尿病症狀,母親帶著我陪她去看病,問診的是一名年輕女醫生。
醫生的華語不是很靈光,但還是嘗試詢問外婆的情況,可惜外婆只會講福建話,開口說了幾句後,醫生一臉無助地看著紅螞蟻的母親問道:「她說什麼啊?」
母親之後就全程充當翻譯,醫生才明白髮生什麼事,並以英語向母親解釋診斷。
20多年後的今天,醫護人員和病患之間「雞同鴨講」的情況有些什麼改變?我們從《海峽時報》日前刊登的兩篇讀者來函可以看出。
外籍和年輕醫護人員難用方言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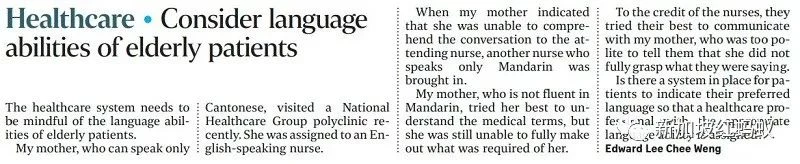
(海峽時報截圖)
一名男子投函寫道,他的母親只會說廣東話,近期到一家綜合診療所看病時,原本被分配到一名講英語的護士。
在老人家表明她無法理解雙方的對話時,另一名講華語的護士過來幫忙,但老人家的華語也不流利,雖然盡力了解護士說出的醫學術語,到頭來仍一知半解。
這名男子表示,他明白護士已經盡全力和他的母親溝通,但母親出於禮貌,沒有告訴她們自己其實沒有完全聽懂她們的話。
他因此問道:
「新加坡醫療系統是否有相關措施,讓病患註明他們首選或傾向使用的語言,以便他們分配到具備適當語言能力的醫護人員?」
這篇讀者來函刊登的兩個星期後,新加坡知名腸胃及肝膽專科顧問醫生韋俊韜也投函《海峽時報》,透露自己的確觀察到這個現象。
他指出,許多醫護人員都是外籍人士,因此無法使用華人方言溝通。
再者,許多年輕一輩的醫生和護士,也遇到這個問題。

有醫生認為,許多醫護人員都是外籍人士,無法用華人方言溝通,而年輕一輩的醫生護士也會遇到這個問題。(聯合早報)
據韋俊韜醫生觀察,醫療機構一般有能以福建話或廣東話溝通的職員,但人數不多。
況且,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完成,需要他們協助與病人溝通的時候,他們未必走得開。
擬定精通方言員工名單可派上用場
上述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語言障礙。它之所以令人感覺難以避免,是因會說方言的新加坡人有逐步下跌的跡象。
新加坡統計局前年發布的2020年人口調查數據顯示,47.6%的受訪華族家庭在家中最常說英語,以華語溝通的家庭則占40.2%。
然而,只有11.8%的華族家庭會在家中說方言,相比2010年的19.2%顯著下滑。

綜合診療所發言人說,他們有一份員工名單,列明曾受訓熟悉各種不同本土語言的員工名字。(聯合早報)
即便如此,新加坡一些醫療機構還是有應對措施,促進雙向溝通。
大巴窯綜合診療所主管陳凱偉(音譯)醫生在回復讀者來函時透露,病患第一次到綜合診所看病時,電子病歷系統都會記錄他們的語言偏好。
他也說,診所也會準備一份員工名單,這些員工都曾接受訓練,熟悉各種不同的本土語言(vernacular languages),有需要時,可以在問診過程幫助只會說方言的病患。
韋俊韜醫生也認同,醫療機構如果都能擬定一份名單,清楚列明精通各個語言和方言的員工和義工,必要時絕對能派上用場。
他說:
「名單上的員工或義工,可在病患前來看病時擔任口譯員,不論是面對面或電話上的解說都能給予幫助。」
不只是院方和病患之間的問題

年長者看病或複診時,是否有其他人陪同?(海峽時報)
誠然,年長者在其他多種場合,也許同樣會碰到「雞同鴨講」的窘境,不過在醫療機構的環境中,這個問題更顯得棘手,因為這關乎老人家的健康,甚至性命。
一篇讀者來函也指出,醫學術語也構成一道障礙。
另一方面,病患「有聽沒有懂」狀況看似單純,也折射出一些社會問題。
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年長者看病或複診時,是否有其他人陪同?
這個問題可能有幾個答案:病患由親友陪同、由女傭陪同,或是獨自一人。
倘若是後兩種情形,老人家就更可能落入無法全然明白醫護人員指示的情況,而除非女傭有相關的語言能力,要求她們當翻譯好像也有些強人所難。
韋俊韜醫生認為,最理想的情況,還是有家人或親戚陪同複診。
他引述個人經歷指出,他的父母只會說廣東話,英語和華語能力欠佳,因此兩老每次要看醫生時,他都會陪同在側。
「這也讓我有機會跟醫生交流,了解他們的病況及治療方案。」
他因此建議,醫生問診前,讓年長病患撥電給孩子或孫子,由他們充當翻譯。
但這麼做的前提是後輩必須能與長輩溝通,唯按照之前引述的統計局的數據,方言的使用似乎已不再那麼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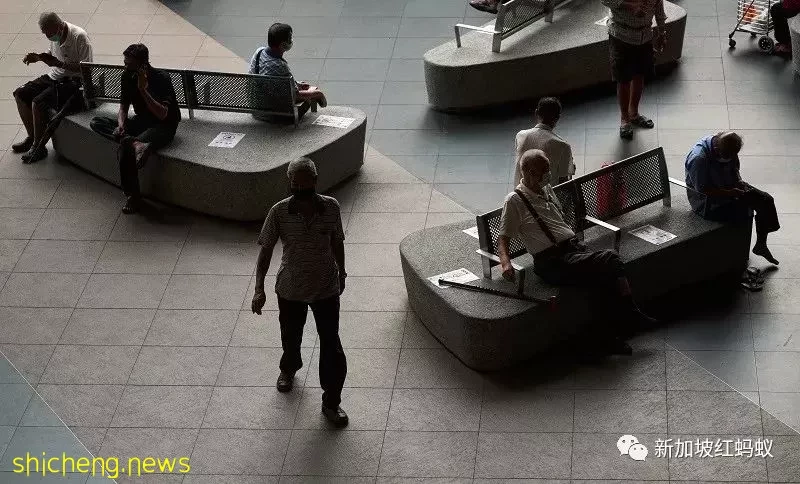
(聯合早報)
就像幫助年長者掌握數碼技能進程中所遇到的挑戰一樣,新加坡邁向超老齡化社會之際,即使面對語言障礙、獨居老人日漸增加的情況,仍應設法確保年長者不會因為某一方面的不足,而無法獲得所需的醫療照顧,甚至漸漸與社會脫節。